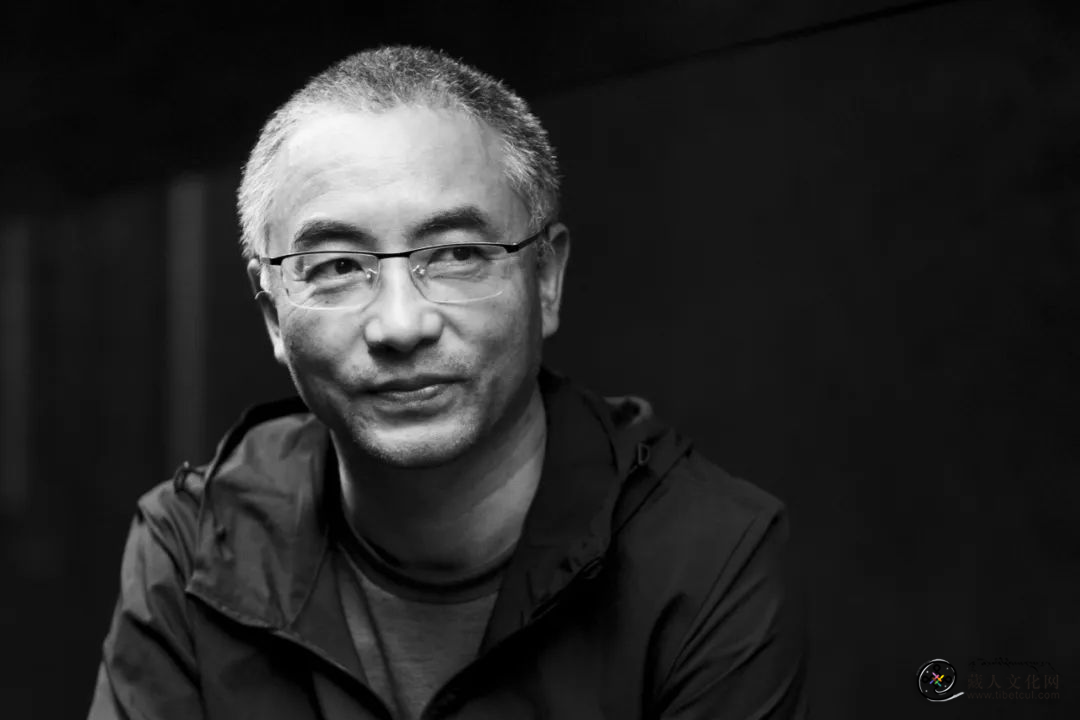еј•иЁҖ
жұүи—ҸдёӨз§ҚиҜӯиЁҖзҡ„дёҚеҗҢзү№иҙЁеҸҠжүҖи•ҙеҗ«зҡ„е®ЎзҫҺзү№еҫҒжһ„жҲҗдәҶ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еӨҡйқўзҡ„еҶҷдҪңз©әй—ҙпјҢиҖҢдёҚеҗҢзҡ„иҜӯиЁҖеӘ’д»ӢеҸҲдёә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ж–Үжң¬зҡ„йҳ…иҜ»дёҺйҳҗеҸ‘жҸҗдҫӣдәҶеӨҡе…ғзҡ„йҖ”еҫ„гҖӮе°Өе…¶еҸҢиҜӯж–ҮеӯҰеҲӣдҪңпјҢд»Ҙе®ғзӢ¬зү№зҡ„еҶҷдҪңе®һи·өжү“з ҙдәҶдёӨз§ҚиҜӯиЁҖд№Ӣй—ҙзҡ„йҡ”йҳӮпјҢе®һзҺ°дәҶж–ҮеӯҰж–Үжң¬зҡ„и·ЁиҜӯйҷ…жөҒеҠЁпјҢиҗҘе»әдәҶдҪңе“ҒйҳҗйҮҠзҡ„еӨҡз»ҙи§ҶйҮҺгҖӮ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дёӯдҪңиҖ…зҡ„иҮӘиҜ‘жҳҜе‘ҲзҺ°еҸҢиҜӯж–Үжң¬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ејҸпјҢиҖҢиҮӘиҜ‘еҸҲдёҚеҗҢдёҺдёҖиҲ¬жҖ§зҡ„зҝ»иҜ‘пјҢж— и®әжҳҜеңЁеҜ№еҶ…е®№зҡ„зҗҶи§ЈдёҠпјҢиҝҳжҳҜеҜ№йЈҺж јзҡ„жҠҠжҸЎд»ҘеҸҠеҲӣдҪңжһ„жҖқзҡ„еҝғзҗҶжңәеҲ¶зӯүеӨҡдёӘж–№йқўиҮӘиҜ‘йғҪеҮёжҳҫдәҶе…¶зү№ж®ҠжҖ§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ҹжҳҜеҰӮжӯӨпјҢд»–зҡ„еҸҢиҜӯж–Үжң¬еҮ д№ҺйғҪжҳҜдҪңиҖ…иҮӘиҜ‘зҡ„з»“жһңпјҢиҖҢиҝҷеҸҲдҪҝд»–е®һзҺ°дәҶж–Үжң¬зҡ„и·ЁиҜӯйҷ…жөҒйҖҡдёҺи·Ёж–ҮеҢ–иЎЁиҫҫгҖӮжҚўеҸҘиҜқиҜҙпјҢеҸҢиҜӯдёә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ҶҷдҪңжҸҗдҫӣдәҶдёҚеҗҢзҡ„еҲӣдҪңи§ҶйҮҺе’Ңйҳ…иҜ»и§Ҷ角并дёҺе…¶иүәжңҜж„ҹжӮҹзӣёиҝһпјҢеҜ№д»–дә§з”ҹзқҖж·ұеҲ»еҪұе“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ҪңиҖ…е…јиҜ‘иҖ…зҡ„еҸҢйҮҚиә«д»ҪгҖҒеҸҢиҜӯиЎЁиҫҫиғҪеҠӣгҖҒзӢ¬зү№зҡ„иүәжңҜж„ҹжӮҹпјҢд»ҘеҸҠиҮӘжҲ‘ж°‘ж—Ҹж–ҮеҢ–дҝ®е…»зӯүиҜёеӨҡеӣ зҙ дҪ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ҢиҜӯе°ҸиҜҙе‘ҲзҺ°еҮәдәҶзӢ¬зү№зҡ„йӯ…еҠӣгҖӮ
дёҖгҖҒ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гҖҒиҮӘиҜ‘дёҺж–Үжң¬йҳ…иҜ»з©әй—ҙзҡ„延еұ•
дәҢеҚҒдё–зәӘе…«еҚҒе№ҙд»Јд»ҘжқҘпјҢ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еңЁжұүи—ҸдёӨз§ҚиҜӯиЁҖеҲӣдҪңдёӯйғҪеҸ–еҫ—дәҶеҸҜе–ңзҡ„жҲҗжһңгҖӮж— и®әжҳҜд»ҘйҘ¶йҳ¶е·ҙжЎ‘гҖҒдјҠдё№жүҚи®©гҖҒ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гҖҒиүІжіўгҖҒеӨ®зҸҚгҖҒйҳҝжқҘзӯүдёәд»ЈиЎЁзҡ„и—Ҹж—ҸеҪ“д»Ј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пјҢиҝҳжҳҜд»Ҙжң—йЎҝ·зҸӯи§үгҖҒж–Ӣжһ—·ж—әеӨҡгҖҒз«ҜжҷәеҳүгҖҒеҫ·жң¬еҠ зӯүдәәдёәд»ЈиЎЁзҡ„еҪ“д»Ји—ҸиҜӯдҪң家зҫӨпјҢ他们йғҪд»ҘдёҚеҗҢзҡ„еӘ’д»ӢжӢ“е®ҪдәҶ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зҡ„иҜӯиЁҖиҫ№з•Ңе’ҢиҜқиҜӯиЎЁиҫҫжңәеҲ¶пјҢдёҚж–ӯдё°еҜҢзқҖ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зҡ„еҶ…ж¶өдёҺеӨ–延гҖӮз”ұдәҺеҸҢиҜӯж•ҷиӮІзҡ„е®һж–ҪдёҺж–ҮеӯҰи·ЁиҜӯйҷ…гҖҒи·Ёж–ҮеҢ–дј ж’ӯзҡ„йңҖиҰҒпјҢеҰӮд»Ҡи®ёеӨҡи—Ҹж—ҸдҪң家йғҪжҠ•иә«еҲ°дәҶ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зҡ„иЎҢеҲ—пјҢиҝҷдёә他们иөўеҫ—дәҶжӣҙдёәе№ҝйҳ”зҡ„иҜ»иҖ…з©әй—ҙе’ҢйҳҗйҮҠз©әй—ҙ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з”ЁжұүиҜӯеҸ‘иЎЁеӨ„еҘідҪңгҖҠдәәдёҺзӢ—гҖӢ并е°Ҷе…¶иҮӘиҜ‘дёәи—Ҹж–Үд»ҘжқҘпјҢд»–д»ҘиҮӘе·ұзҡ„еҸҢиҜӯдјҳеҠҝе’ҢиҮӘиҜ‘зӯ–з•Ҙе°ҪеҠӣдҪҝе…¶е°ҸиҜҙд»ҘеҸҢиҜӯж–Үжң¬е‘ҲзҺ°пјҢеј•еҸ‘дәҶдёҚеҗҢиҜӯз§Қзҡ„иҜ»иҖ…зҡ„еҫ®еҰҷиҖҢж·ұеҲҮзҡ„жғ…ж„ҹе…ұйёЈгҖӮ
еҸҢиҜӯж–Үжң¬зҡ„е‘ҲзҺ°жүӢж®өеңЁдәҺдҪңиҖ…зҡ„иҮӘиҜ‘пјҢж— и®әжҳҜжұүиҜ‘и—ҸпјҢиҝҳжҳҜи—ҸиҜ‘жұүпјҢд»ҺдҪңиҖ…е…јиҜ‘иҖ…зҡ„еҸҢйҮҚиә«д»Ҫзү№еҫҒе’ҢиҜ‘жң¬зҡ„дё»дҪ“жҖ§иҖҢиЁҖпјҢиҮӘиҜ‘ж— и®әеңЁжҖқз»ҙж–№ејҸгҖҒд»·еҖјж ҮеҮҶгҖҒеҶҷдҪңж„ҸеӣҫгҖҒе®ЎзҫҺи¶Је‘ігҖҒиҜӯиЁҖйЈҺж јгҖҒзҝ»иҜ‘зӯ–з•Ҙзӯүж–№йқўйғҪдёҚеҗҢдёҺдёҖиҲ¬жҖ§зҡ„иҜ‘дҪңпјҢеңЁдёҖе®ҡж„Ҹд№үдёҠпјҢеүҚиҖ…жҳҜдҪңиҖ…еҶҷдҪңйЈҺж јзҡ„дёҖз§Қ延з»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ҪңдёәдҪңиҖ…е…јиҜ‘иҖ…з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ңЁиҮӘиҜ‘е®һи·өдёӯеҜ№еҺҹж–Үзҡ„зҗҶи§Је’ҢдёҖиҲ¬жҖ§зҝ»иҜ‘жҳҜдёҚеҗҢзҡ„гҖӮеңЁеҝғзҗҶеұӮйқўдёҠпјҢе…¶дёҺдҪңиҖ…зҡ„иүәжңҜж„ҹзҹҘе’ҢеҝғзҗҶжңәеҲ¶зҙ§еҜҶзӣёиҝһпјӣеңЁеҲӣдҪңе®һи·өдёӯпјҢиҮӘиҜ‘дёҺеҶҷдҪңеҸҲжһ„жҲҗдәҶдә’дёәеҸӮз…§зҡ„иЎҘе……е…ізі»пјҢжҳҜдёҖз§ҚеҶҷдҪңйЈҺж јзҡ„延з»ӯпјӣиҖҢеңЁиҜ»иҖ…зҡ„йҳ…иҜ»и§ҶйҮҺдёӯпјҢж–Үжң¬д»ҘдёҚеҗҢиҜӯз§Қе‘ҲзҺ°пјҢе…·еӨҮдәҶдёҚеҗҢзҡ„жҺҘеҸ—и§Ҷи§’гҖӮеӣ жӯӨпјҢиҮӘиҜ‘дёҺеҲӣдҪң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иә«дёҠжһ„жҲҗдәҶеҜҶеҲҮиҖҢеӨҚжқӮзҡ„иғҪеҠЁе…ізі»пјҢеҚіе®ғжҳҜдёҖз§ҚйҖҡиҝҮдҪңиҖ…дёӘдәәзҡ„и·ЁиҜӯйҷ…е®һи·өдҪҝж–Үжң¬еңЁдёҚеҗҢиҜӯеўғдёӯеҫ—д»ҘеҶҚеәҰ延еұ•пјҢд»ҺиҖҢдҪҝж–Үжң¬ж„Ҹд№үеҶҚз”ҹзҡ„иҝҮзЁӢгҖӮиҝҷдёҚд»…д»…жҳҜдёӨз§ҚиҜӯиЁҖд№Ӣй—ҙз®ҖеҚ•зҡ„иҪ¬еҢ–е’ҢдёӨз§Қж–Үжң¬ж„Ҹд№үзӯүеҖјзҡ„й—®йўҳпјҢжӣҙжҳҜж¶үеҸҠеҲ°дәҶдҪңиҖ…зҡ„зҝ»иҜ‘з«Ӣеңәе’Ңи·ЁиҜӯйҷ…зҡ„дј ж’ӯи§ҶйҮҺгҖӮ
дј—жүҖе‘ЁзҹҘпјҢж–ҮеӯҰжҳҜиҜӯиЁҖзҡ„иүәжңҜпјҢд№ҹжҳҜдёҖз§Қе®ЎзҫҺж„ҸиҜҶеҪўжҖҒ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ҮеӯҰе®ЎзҫҺеңЁ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жҳҜеҜ№иҜӯиЁҖеҗ„еұӮж¬Ўзҡ„е®ЎзҫҺпјҢиҖҢиҜӯиЁҖеҸҲе…·жңүеҺҶеҸІжҖ§е’Ңе·®ејӮжҖ§пјҢе…¶дёҚд»…дёҺз”ҹжҙ»д№ жҖ§гҖҒзӨҫдјҡз»“жһ„гҖҒжғіеғҸжҖқз»ҙжҒҜжҒҜзӣёиҝһпјҢд№ҹз”ұдәҺ“дәәзҡ„иҜӯиЁҖдёҺдәәзҡ„ж„ҹи§үгҖҒзҹҘи§үгҖҒжғіеғҸзҗҶи§ЈзӯүеҝғзҗҶжңәиғҪжҳҜеҗҢдёҖзҡ„гҖӮиҜӯиЁҖжҳҜеҶ…еңЁдёҺдәәзҡ„ж„ҹи§үзҡ„пјҢе°ұд»ҘдёӘдҪ“зҡ„дәәзҡ„иҜӯиЁҖеҸ‘еұ•иҖҢиЁҖпјҢд»–зҡ„иҜӯиЁҖдёҺд»–зҡ„ж„ҹи§үжҳҜдёҖиҮҙзҡ„гҖӮ”[1]дәҺжҳҜпјҢиҜӯиЁҖдёҺж–ҮеӯҰд№Ӣй—ҙд№ҹдёҚд»…жҳҜиЎЁзҺ°е·Ҙе…·жҲ–иҜӯжі•з»“жһ„зҡ„з®ҖеҚ•з»„еҗҲпјҢжӣҙдёәйҮҚиҰҒзҡ„жҳҜиҜӯиЁҖдёҺдәәзұ»жҖқз»ҙе’Ңдәәзұ»еӯҳеңЁзҡ„ж·ұеұӮе…ізі»жүҖеҶіе®ҡзҡ„иЁҖиҜӯиЎЁиҫҫдёҺжғ…ж„ҹдё–з•Ңд№Ӣй—ҙзҡ„е…ізі»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ҚеҗҢж–ҮеҢ–дёӯдёҚеҗҢзҡ„иҜӯиЁҖ规иҢғгҖҒдёҚеҗҢиҜӯиЁҖеҶ…йғЁзҡ„йҖүиҜҚгҖҒеҸҘжі•гҖҒз« жі•гҖҒдҝ®иҫһзӯүдёҠзҡ„зӣёејӮпјҢд»ҘеҸҠиҜ‘иҖ…иҜ‘жң¬зҡ„дё»дҪ“жҖ§дёҺиҜ»иҖ…зҡ„жҺҘеҸ—и§ҶзӮ№йғҪдҪҝеҸҢиҜӯж–Үжң¬е…·еӨҮдәҶдёҚеҗҢзҡ„йҳҗйҮҠиҜӯеўғгҖӮеҪ“然пјҢиҮӘиҜ‘е®һи·өдёӯз”ұдәҺиҜ‘иҖ…зҡ„зү№ж®Ҡиә«д»Ҫе’Ңе…¶еҜ№е°ҸиҜҙеҶ…еңЁзҡ„жҠҠжҸЎпјҢд№ҹеҜјиҮҙдәҶж–Үжң¬д№Ӣй—ҙзҡ„дёҚеҜ№зӯүе…ізі»гҖӮеҰ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ҠжөҒжөӘжӯҢжүӢзҡ„жўҰгҖӢгҖҠж•Ій—ЁеЈ°е“ҚдәҶгҖӢгҖҠжІЎжңүдёӢйӣӘзҡ„еҶ¬еӨ©гҖӢзӯүе°ҸиҜҙзҡ„еҸҢиҜӯж–Үжң¬иҷҪж•…дәӢе®№йҮҸдёҺжғ…иҠӮеҶ…е®№жңӘеҸ‘з”ҹеҸҳеҢ–пјҢдҪҶдёӨз§Қж–Үжң¬зҡ„еҸҘејҸиЎЁиҫҫе’Ңж–ҮдҪ“йЈҺж јжҳҫ然еӯҳжңүе·®ејӮпјҢз»ҷиҜ»иҖ…д»ҘдёҚеҗҢзҡ„йҳ…иҜ»ж„ҹеҸ—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ҸҢиҜӯж–Үжң¬зҡ„дёҚеҗҢиҜӯиЁҖж„ҹеҸ—е®ЎзҫҺ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ҲӣдҪңдёӯ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Қдә’иЎҘпјҢдёәйҳ…иҜ»йҳҗйҮҠз©әй—ҙжҸҗдҫӣдәҶдёҚеҗҢзҡ„еҸӮз…§зі»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ҡ“еҜ№жҲ‘жқҘиҜҙпјҢи—ҸиҜӯеҶҷдҪңдёҺ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д№Ӣй—ҙжҳҜдёҖз§Қдә’иЎҘе…ізі»пјҢиҝҷд№ҹжҳҜи®©жҲ‘зҡ„дҪңе“ҒеҢәеҲ«дәҺеҸӘз”Ёи—ҸиҜӯеҶҷдҪңпјҢжҲ–иҖ…еҸӘз”Ё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зҡ„дҪң家зҡ„дёҖдёӘдјҳеҠҝгҖӮеҪ“е®ғ们碰ж’һеҮәзҒөж„ҹзҡ„зҒ«иҠұпјҢиҝҷж ·зҡ„еҲӣдҪңдјҡи®©дҪ зҡ„дҪңе“Ғе…·жңүдёҖз§Қж„ҸжғідёҚеҲ°зҡ„ж•ҲжһңгҖӮ”[2]еӣ жӯӨ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иҮӘиҜ‘жүҖе‘ҲзҺ°зҡ„еҸҢиҜӯж–Үжң¬иҮӘ然еҪ°жҳҫдәҶдёҚеҗҢиҜӯиЁҖзҡ„зҫҺеӯҰзү№иҙЁпјҢеңЁдёҚеҗҢиҜӯз§Қзҡ„иҜ»иҖ…е’ҢйҳҗйҮҠз©әй—ҙеҶ…дә§з”ҹдәҶдёҚеҗҢзҡ„е®ЎзҫҺж•Ҳжһң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дёҚд»…дҪ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ж„ҹеҸ—зқҖдёҚеҗҢиҜӯиЁҖж–ҮеҢ–зі»з»ҹзҡ„ејӮиҙЁжҖ§дёҺеҗҢдёҖжҖ§пјҢиҖҢдё”иҮӘиҜ‘иҖҢжҲҗзҡ„еҸҢиҜӯж–Үжң¬д№Ӣй—ҙзҡ„дә’иЎҘжӣҙжҳҜдёәд»–дҫӣз»ҷдәҶдё°еҜҢзҡ„еҶҷдҪңиө„жәҗе’ҢдјҳеҠҝгҖӮ
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дёӯжҜ”иө·йӮЈдәӣдёӘдәәеҢ–иүІи°ғжө“еҺҡзҡ„жұүиҜӯе°ҸиҜҙиҖҢиЁҖпјҢж—©жңҹзҡ„жңүдәӣи—ҸиҜӯе°ҸиҜҙдёӯзҺ°е®һеӣ зҙ жӣҙдёәзӘҒеҮәпјҢжү№еҲӨжҢҮеҗ‘д№ҹжӣҙдёәй”ӢиҠ’пјҢиҝҷеҸҲдҪ“зҺ°зқҖд»–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зҡ„дёҖз§ҚйҖүжӢ©жҖ§зӯ–з•ҘгҖӮеҰ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и—ҸиҜӯе°ҸиҜҙгҖҠеҹҺеёӮз”ҹжҙ»гҖӢгҖҠжҳҹжңҹж—ҘгҖӢгҖҠеҠһе…¬е®Өи§Ғй—»гҖӢгҖҠжҲ‘зҡ„ж¬Ўд»ҒеҚ“зҺӣгҖӢгҖҠеҺ»жіҪеҪ“гҖӢгҖҠжҲҝеұӢгҖӢгҖҠд№һдёҗгҖӢгҖҠж¬ўе–ңгҖӢзӯүдёӯдҪңиҖ…д»Ҙжү№еҲӨзҺ°е®һдё»д№үзҡ„жүӢжі•еҸҷеҶҷдәҶдәәжҖ§зҡ„иҷҡдјӘдёҺдё‘йҷӢгҖҒеҹҺеёӮеҢ–иҝӣзЁӢдёӯзҡ„ж–ҮеҢ–еҶІзӘҒгҖҒж°‘ж—Ҹж•ҷиӮІзҡ„еӣ°еўғгҖҒд№Ўеңҹдәәзҡ„еҶ…еҝғжғ…ж„ҹгҖҒеҪ“дёӢж°‘ж—Ҹж–ҮеҢ–зҡ„еӨұиҗҪзӯүзӨҫдјҡй—®йўҳ并еҜ№жӯӨзұ»й—®йўҳиҝӣиЎҢдәҶзҠҖеҲ©ең°жү№еҲӨ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иҝҷдәӣи—ҸиҜӯе°ҸиҜҙеңЁзӣёеҪ“зЁӢеәҰдёҠиҫғдёәйІңжҳҺең°иЎЁзҺ°дәҶдҪңиҖ…еҜ№зҺ°е®һзӨҫдјҡзҡ„и§Ӯз…§пјҢд№ҹиҝҺеҗҲдәҶи—ҸиҜӯеҪ“д»Је°ҸиҜҙзҡ„еҲӣдҪңдё»жҪ®гҖӮ然иҖҢпјҢжӯӨзұ»жү№еҲӨзҺ°е®һдё»д№үжүӢжі•зҡ„е°ҸиҜҙ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дёӯиҫғдёәе°‘и§ҒпјҢе…¶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жӣҙеӨҡең°е…іжіЁдёӘдәәеҢ–е’ҢиүәжңҜеҢ–зҡ„иЎЁиҫҫж–№ејҸгҖӮдҪңиҖ…д№ҹжӣҫиҜҙпјҡ“жңүдәӣе°ҸиҜҙжҲ‘еҸӘдјҡз”Ёи—Ҹж–ҮеҶҷгҖӮж–ҮеӯҰеңЁи—ҸеҢәд»Қ然具жңүжү№еҲӨзҺ°е®һдё»д№үзҡ„еҠҹиғҪпјҢиҝҷз§ҚеҠҹиғҪеңЁж•ҙдёӘдё–з•Ңж–ҮеӯҰж јеұҖдёӯеҸҜиғҪйҖҗжӯҘејұеҢ–пјҢдҪҶеңЁи—Ҹж—ҸиҝҳжңүжҜ”иҫғйҮҚиҰҒзҡ„дҪңз”ЁгҖӮеҫҲеӨҡжҜҚиҜӯдҪң家йҖҡиҝҮж–ҮеӯҰиЎЁиҫҫиҮӘе·ұпјҢиЎЁиҫҫеҜ№зҺ°е®һзҡ„зңӢжі•гҖӮиҜ»иҖ…д№ҹйҖҡиҝҮ他们зҡ„дҪңе“ҒеҜ№зҺ°е®һиҝӣиЎҢеҸҚжҖқгҖӮ”[3]еӣ жӯӨпјҢдҪңиҖ…зҡ„ж–ҮеҢ–з«Ӣеңәе’Ң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зӯ–з•Ҙд№ҹ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ҚеҗҢжһ„е…ізі»пјҢеңЁдё»йўҳйҖүжӢ©гҖҒиҜӯиЁҖиЎЁиҫҫгҖҒзӨҫдјҡж•ҲзӣҠж–№йқўдҪңиҖ…жңүзқҖиҫғдёәжҳҺзЎ®зҡ„еҶҷдҪңж„ҸиҜҶпјҢдҪңиҖ…жүҖжңҹеҫ…зҡ„йҳ…иҜ»и§ҶйҮҺеҜ№д»–зҡ„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дә§з”ҹзқҖж·ұеҲ»еҪұе“ҚпјҢд»ҘиҮҙдҪңиҖ…йҮҮеҸ–дәҶдёҚеҗҢзҡ„йҖүжӢ©жҖ§иЁҖиҜҙж–№ејҸе’ҢеҶҷдҪңзӯ–з•ҘгҖӮ
еҸҢиҜӯиғҪеҠӣдҪ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е…·еӨҮдәҶдёӨз§ҚиҜӯиЁҖзҡ„еҶҷдҪңз©әй—ҙпјҢдҪҝд»–иғҪжӣҙеҘҪең°жҠҠжҸЎдё–з•ҢгҖҒи§ӮеҜҹз”ҹжҙ»гҖҒиЎЁиҫҫжғ…ж„ҹгҖӮжӯЈеҰӮжңүз ”з©¶иҖ…з§°пјҢ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жҠҠдёҚеҗҢзҡ„жҖқз»ҙж–№ејҸгҖҒдёҚеҗҢзҡ„и§ӮеҜҹдё–з•Ңзҡ„ж–№жі•иҒ”зі»еңЁдёҖиө·пјҢиҖҢиҝҷпјҢе°ҶдјҡдҪҝдёҖз§Қж–°зҡ„и®ӨиҜҶж°ҙе№ідә§з”ҹгҖӮжүҖд»ҘпјҢеҫҲеҘҪең°жҺҢжҸЎеҸҰдёҖз§ҚиҜӯиЁҖпјҢжҳҜдёҖз§Қеё®еҠ©пјҢдёҖз§Қйҷ„еҠ дҪңз”ЁпјҢжҳҜд»ҺиҜӯиЁҖе’ҢеҪўиұЎдёҠеҺ»и§ӮеҜҹдё–з•Ңзҡ„дёҖз§ҚиЎҘе……жүӢж®өгҖӮ”[4]еӣ жӯӨ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е’ҢиҮӘиҜ‘зӯ–з•ҘдёҚд»…е‘ҲзҺ°дәҶеҗҢдёҖе°ҸиҜҙдёҚеҗҢиҜӯиЁҖйЈҺж јзҡ„дёӨз§Қж–Үжң¬пјҢиҖҢдё”д»ҘдёҚеҗҢзҡ„иҜӯиЁҖзҫҺеӯҰзү№еҫҒжқҘдј йҖ’дҪңиҖ…иҮӘе·ұзҡ„иүәжңҜж„ҹжӮҹпјҢдёәе…¶иөўеҫ—дәҶжӣҙдёәж—·йҳ”зҡ„йҳ…иҜ»з©әй—ҙпјҢд№ҹдёәжұүи—ҸдёӨз§ҚиҜӯиЁҖд№Ӣй—ҙжҗӯиө·дәҶдёҖеә§дәӨжөҒдёҺе…ұз”ҹзҡ„жЎҘжўҒгҖӮ
дәҢгҖҒйӯ”е№»гҖҒиҚ’иҜһзҡ„жӮІеү§еҸҠе…¶еҗҺзҺ°д»Јеӣ зҙ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ҮӘдәҢеҚҒдё–зәӘд№қеҚҒе№ҙд»ЈејҖе§Ӣд»Ҙжұүи—ҸдёӨз§ҚиҜӯиЁҖиҝӣиЎҢеҲӣдҪңпјҢеңЁиҝ‘дёүеҚҒеӨҡе№ҙзҡ„е°ҸиҜҙеҶҷдҪңиҝҮзЁӢдёӯдёҚж–ӯең°жҺўзҙўзқҖйҖӮеҗҲиҮӘе·ұзҡ„иЎЁиҫҫж–№ејҸгҖӮеңЁеҲӣдҪңеҲқжңҹ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еҲ°дәҶдёӯеӣҪ“‘е…Ҳй”Ӣж–ҮеӯҰ’”[5]е’ҢдәҢеҚҒдё–зәӘдёӢеҚҠеҸ¶еҗҺд»ЈзҺ°д»Јж–ҮеӯҰзҡ„ж·ұеҲ»еҪұе“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йӯ”е№»зҡ„гҖҒиұЎеҫҒзҡ„гҖҒиҚ’иҜһзҡ„гҖҒеӯӨзӢ¬зҡ„гҖҒжҡҙеҠӣзҡ„зӯүеӨҡз§ҚеҗҺзҺ°д»Јеӣ зҙ дәӨз»ҮеңЁд»–зҡ„ж—©жңҹеҸҢиҜӯе°ҸиҜҙдёӯ并иҗҘе»әдәҶе…¶еҸҷдәӢдҪңе“Ғзҡ„еҗҺзҺ°д»ЈзҫҺеӯҰе“Ғж јгҖӮеҰӮгҖҠеІ—гҖӢдёӯ“еІ—”зҡ„еҮәзҺ°дёҺж¶ҲеӨұпјӣгҖҠжөҒжөӘжӯҢжүӢзҡ„жўҰгҖӢдёӯж¬Ўд»Ғзҡ„иҝҪжұӮдёҺжңҖз»Ҳзҡ„еӨұиҗҪпјӣгҖҠжңҲдә®гҖӢдёӯжңҲдә®йўңиүІзҡ„еҸҳеҢ–еҸҠе…¶еҜ“ж„ҸпјӣгҖҠиҜұжғ‘гҖӢдёӯдё»дәәе…¬еҳүжҙӢдё№еўһзҡ„жӯ»иҖҢеӨҚз”ҹпјӣгҖҠдёҖйЎөгҖӢдёӯж—¶й—ҙзҡ„й”ҷдҪҚдёҺеҸҰзұ»дё–з•Ңзҡ„е‘ҲзҺ°пјӣгҖҠеҚҲеҗҺгҖӢдёӯе°‘е№ҙжҳӮжң¬жўҰе№»зҡ„жёёеҺҶпјӣ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жҙӣжЎ‘дёҺжӯ»иҖ…д№Ӣй—ҙзҡ„еҜ№иҜқзӯүзӯүйғҪдёҚеҗҢзЁӢеәҰең°дҪ“зҺ°дәҶ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дёӯйӯ”е№»иүІеҪ©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ҡ“йӯ”е№»зҺ°е®һдё»д№үеҜ№дәҺи—ҸеҢәж–ҮеҢ–гҖҒи—ҸеҢәдҪң家ж·ұжңүеҪұе“ҚпјҢдёҠдё–зәӘ80е№ҙд»ЈејҖе§ӢеңЁж•ҙдёӘдёӯж–ҮеңҲеҪұе“ҚеӨ§пјҢиҺ«иЁҖгҖҒйҳҺиҝһ科йғҪжӣҫе°қиҜ•пјҢзңҹжӯЈеңЁдёӯеӣҪз”ҹж №жҳҜеңЁиҘҝи—ҸгҖӮеҪ“е№ҙ“иҘҝи—Ҹж–°е°ҸиҜҙ”зӣӣиЎҢпјҢе°Өе…¶д»Ҙ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дёәд»ЈиЎЁзҡ„е…·жңүйӯ”е№»гҖҒиҚ’иҜһиүІеҪ©зҡ„е°ҸиҜҙпјҢж·ұеҲ»еҪұе“ҚеҲ°дәҶи—ҸиҜӯеҶҷдҪңгҖӮйҖҡиҝҮиҝҷдәӣжұүиҜӯе°ҸиҜҙпјҢдёӯеӣҪзҡ„йӯ”е№»зҺ°е®һдё»д№үжҒ°жҒ°жҺҘйҖҡдәҶ马尔е…Ӣж–ҜгҖҒиғЎе®ү·йІҒе°”зҰҸгҖӮ马尔е…Ӣж–Ҝе°ҸиҜҙйҮҢжүҖжңүзҰ»еҘҮиҚ’иҜһзҡ„жғ…иҠӮгҖҒз»ҶиҠӮпјҢйғҪжңүзҺ°е®һдҫқжҚ®пјҲ马尔е…Ӣж–ҜеҺ»дё–ж¶ҲжҒҜдј жқҘ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ҢиҝҷжҳҜд»–еҪ“еӨ©еҗ¬еҲ°зҡ„жңҖеқҸзҡ„ж¶ҲжҒҜпјүпјҢи—ҸеҢәдҪң家дҪңе“Ғдёӯзҡ„жүҖи°“йӯ”е№»пјҢжҲ‘и§үеҫ—д№ҹжҳҜжңүзҺ°е®һдҫқжҚ®зҡ„гҖӮеӣ дёәеңЁи—ҸеҢәзҺ°е®һз”ҹжҙ»е°ұжҳҜиҝҷж ·пјҢи—ҸеҢәдәәд№ҹзӣёдҝЎйӮЈдәӣз•ҘеёҰйӯ”е№»зҡ„зҺ°е®һе°ұжҳҜзңҹе®һзҡ„зҺ°е®һпјӣеҲ«дәәзңӢжқҘжҳҜйӯ”е№»зҡ„пјҢд»–зңӢжқҘжҳҜзңҹе®һзҡ„гҖӮи—Ҹж—Ҹзҡ„еҸІд№ҰпјҢдёҚеӨӘеғҸдёҘи°Ёзҡ„еҺҶеҸІеӯҰпјҢи—Ҹж—ҸеҸІд№ҰжҳҜж–ҮеӯҰи‘—дҪңпјҢзңӢиө·жқҘдјјд№ҺжҳҜйӯ”е№»зҡ„пјҢеңЁдёҘи°ЁйҮҢеҠ иҝӣдәҶйӯ”е№»зҡ„еӣ зҙ пјӣеңЁж°‘й—ҙзҷҫ姓讲иҝ°еҺҶеҸІж•…дәӢж—¶д№ҹдјҡе°Ҷйӯ”е№»еҠ иҝӣеҺ»пјӣеҶҷеҺҶеҸІйўҳжқҗзҡ„дҪңиҖ…д№ҹдјҡиҝҷж ·пјҢ并且ж·ұдҝЎдёҚз–‘гҖӮе°Ҫз®ЎеҪ“д»ЈеҺҶеҸІеӯҰиҖ…еҜ№жӯӨжңүеҸҚжҖқгҖӮиҝҷжҳҜйӯ”е№»зҺ°е®һдё»д№үиғҪеӨҹз”ҹж №зҡ„дёҖдёӘж–ҮеҢ–еҹәзЎҖгҖӮ”[6]з”ұжӯӨ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дҪңиҖ…еҜ№“йӯ”е№»”зҡ„и®ӨзҹҘж—ўжқҘиҮӘдәҺеҜ№еӨ–еӣҪж–ҮеӯҰзҡ„жҺҘеҸ—пјҢд№ҹжқҘиҮӘдәҺеҜ№жң¬еңҹеҸҷдәӢдј з»ҹзҡ„и®ӨзҹҘпјҢе°Өе…¶еҗҺиҖ…жӣҙеҘҪең°дҪҝд»–жҢ–жҺҳжң¬еңҹеӣ зҙ е»әз«ӢдәҶе…·жңүжң¬еңҹиүІеҪ©зҡ„йӯ”е№»еҸҷдәӢйЈҺж јгҖӮд№ҹе°ұжҳҜиҜҙпјҢдҪңиҖ…еҜ№дәҺиҮӘиә«дј з»ҹж–ҮеҢ–зү№еҫҒзҡ„зҗҶи§Је’Ңд»–еҜ№еӨ–жқҘеӣ зҙ зҡ„жҺҘеҸ—дҪҝе…¶е°ҸиҜҙдёӯзҡ„йӯ”е№»иүІеҪ©дёҺж°‘ж—Ҹж–ҮеҢ–зӣёиҝһе‘ҲзҺ°еҮәдәҶдёҚеҗҢзҡ„зҫҺеӯҰйЈҺж јгҖӮгҖҠеҳӣе‘ўзҹігҖҒ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зӘҒеҮәең°еұ•зҺ°дәҶиҝҷдёҖйЈҺж јзү№еҫҒпјҢиҝҷдёҖе°ҸиҜҙеҸҷиҝ°дәҶдёҖеҲҷ“йҳҙйҳідёӨз•Ң”д№Ӣй—ҙзҡ„ж•…дәӢгҖӮжӯӨзұ»еҸҷдәӢеңЁи—Ҹж—Ҹж°‘й—ҙж–ҮеӯҰгҖҠж јиҗЁе°”зҺӢдј гҖӢе’ҢгҖҠе°ёиҜӯж•…дәӢгҖӢзӯүдёӯеӨ§йҮҸеӯҳеңЁпјҢеңЁи—Ҹж—ҸеҸӨе…ёдҪң家ж–ҮеӯҰдёӯд№ҹеҸҜи§ҒеҲ°пјҢжҳҜж°‘ж—Ҹж–ҮеӯҰиө„жәҗдёӯзҡ„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еҪ°жҳҫзқҖе…¶еҲ«е…·дёҖж јзҡ„еҸҷдәӢйЈҺж ј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ҳиҜҙпјҡ“80е№ҙеҲқеҮәзҺ°дәҶеҫҲеӨҡе°ҸиҜҙжөҒжҙҫпјҢеңЁи—ҸеҢәйқһеёёжөҒиЎҢзҡ„пјҢиҜ„и®әз•Ңз•Ңе®ҡзҡ„е°ұжҳҜйӯ”е№»зҺ°е®һдё»д№үпјҢеғҸ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зӯүгҖӮжҲ‘еҲҡејҖе§ӢеҶҷдҪңж—¶д№ҹеҶҷдәҶеҫҲеӨҡйӮЈз§ҚдёңиҘҝгҖӮеӣ дёәд»Һе°Ҹеҗ¬еҲ°зҡ„ж•…дәӢгҖҒиҜ»еҲ°зҡ„ж°‘й—ҙдј иҜҙпјҢд»ҘеҸҠж–ҮеҢ–зҡ„жёҠжәҗдёӯиҷҡе№»зҡ„дёңиҘҝеӨӘеӨҡдәҶпјҢжңүиҝҷж ·зҡ„еңҹеЈӨгҖӮ”[7]еӣ жӯӨпјҢеҰӮжһңиҜ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жңҹеҶҷдҪңдёӯеҸ—еҲ°дәҶйӯ”е№»зҺ°е®һдё»д№үжҲ–дәҢеҚҒдё–зәӘе…«еҚҒе№ҙд»Ј“иҘҝи—Ҹж–°е°ҸиҜҙ”зҡ„еҪұе“Қиҫғж·ұпјҢйӮЈд№ҲеңЁеҗҺжңҹзҡ„дёҖдәӣе°ҸиҜҙдёӯпјҢйӯ”е№»дёҚд»…д»…жҳҜдёҖз§ҚжүӢжі•е’ҢеҪұе“Қ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з§ҚеҹәдәҺжң¬еңҹж–ҮеҢ–иҖҢз”ҹзҡ„ж–ҮеӯҰдј з»ҹзҡ„еӣһеҪ’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з§Қдәәзү©еӯҳеңЁзҡ„зҠ¶жҖҒдёҺжҖқз»ҙж–№ејҸзҡ„е‘ҲзҺ°гҖӮз”ұжӯӨпјҢжҲ‘们иғҪеҸ‘зҺ°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дёӯзҡ„йӯ”е№»жҳҜдёҖз§ҚеҹәдәҺи·Ёж–ҮеҢ–гҖҒи·Ёж–ҮеӯҰдәӨжөҒе’ҢеҪұе“ҚдёӢжҝҖеҸ‘зҡ„жң¬еңҹдҪң家иҮӘи§үзҡ„иҮӘжҲ‘зҗҶи§ЈиҝҮзЁӢгҖӮ
еҜ»жүҫжҳ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дёӯ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ҜҚйўҳ[8]пјҢиҖҢеҜ»жүҫдёӯзҡ„еӣ°иӢҰдёҺиҷҡж— еҲҷеҮёеҮәдәҶе…¶е°ҸиҜҙдёӯзҡ„иҚ’иҜһдё»йўҳгҖӮ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дёӯпјҢгҖҠжөҒжөӘжӯҢжүӢзҡ„жўҰгҖӢдёӯжӯҢжүӢж¬Ўд»ҒиҝҪжўҰеҺҶзЁӢжүҖеҪ°жҳҫзҡ„еҜ»жўҰд№Ӣеҫ’еҠіпјӣгҖҠеҜ»и®ҝйҳҝеҚЎеӣҫе·ҙгҖӢдёӯйҳҝеҚЎеӣҫе·ҙзҡ„дәәзү©еҪўиұЎеңЁеҮ еәҰдёҚеҗҢзҡ„еҸҷиҝ°дёӯжјӮ移дёҚе®ҡжңҖз»ҲйғҪж— жі•зЎ®з«ӢдёҖдёӘзңҹе®һеҸҜж„ҹзҡ„дәәзү©еҪўиұЎпјӣгҖҠеҜ»жүҫжҷәзҫҺжӣҙзҷ»гҖӢдёӯжұҹеӨ®зӯүдәәиӢҰиӢҰеҜ»жүҫжү®жј”жҷәзҫҺжӣҙзҷ»зҡ„жј”е‘ҳпјҢжңҖз»ҲиҝҳжҳҜжңӘиғҪйҒӮж„ҝпјӣгҖҠйҷҢз”ҹдәәгҖӢдёӯ“йҷҢз”ҹдәә”дёәеҜ»жүҫ第дәҢеҚҒдёҖдёӘеҚ“зҺӣжқҘеҲ°дәҶжқ‘еӯҗпјҢжңҖз»ҲеҜ»и§…ж— жһңзӯүеҸҷдәӢеңЁдёҚеҗҢзЁӢеәҰең°ж¶үеҸҠеҲ°дәҶж— ж„Ҹд№үзҡ„иҚ’иҜһдё»йўҳгҖӮжӯӨеӨ–пјҢгҖҠеҸҜжҖ•зҡ„еӨңжҷҡгҖӢгҖҠй»Ҝж·Ўзҡ„еӨ•йҳігҖӢгҖҠиҜ—дәәд№Ӣжӯ»гҖӢгҖҠжІЎжңүдёӢйӣӘзҡ„еҶ¬еӨ©гҖӢгҖҠеҲҮеҝ е’Ңд»–зҡ„е„ҝеӯҗзҪ—дё№гҖӢгҖҠж•Ій—ЁеЈ°е“ҚдәҶгҖӢзӯүд№ҹйғҪи§ҰеҸҠдәҶдәәзү©еҶ…еҝғдё–з•Ңзҡ„жҒҗжғ§гҖҒеӯӨзӢ¬гҖҒз„Ұиҷ‘дёҺжҡҙеҠӣпјӣиҖҢеңЁгҖҠзү§зҫҠе°‘е№ҙд№Ӣжӯ»гҖӢгҖҠзҘһеҢ»гҖӢгҖҠйҷҢз”ҹдәәгҖӢгҖҠе°ёиҜӯж•…дәӢпјҡжһӘгҖӢгҖҠдёҖзҜҮе°ҸиҜҙеҸҠе…¶дёӨз§Қз»“е°ҫгҖӢзӯүдёӯдҪңиҖ…еҸҲе°Ҷдё»дәәе…¬зҪ®дәҺдёҖдёӘеӯӨз«Ӣж— жҸҙзҡ„еӨ„еўғпјҢеҮёжҳҫдәҶдәәзү©з”ҹеӯҳзҡ„иҷҡж— дёҺиҚ’иҜһ[9]гҖӮ
еҰӮжһңиҜ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жңҹеҸҢиҜӯе°ҸиҜҙдёӯиҚ’иҜһзҡ„жӮІеү§иҝҳе…·еӨҮдәӣи®ёеҙҮй«ҳзҡ„ж·ұеәҰпјҢйӮЈд№Ҳиҝ‘е№ҙжқ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дёӯзҡ„жӮІеү§еҚҙжӣҙеӨҡең°йҖҸйңІеҮәдәҶдёҖз§ҚжІЎжңүжҝҖзғҲеҶІзӘҒзҡ„еҒ¶з„¶жҖ§е’Ңе№іж·ЎжҖ§гҖӮгҖҠжҷ®еёғгҖӢдёӯжҷ®еёғжқҖжӯ»дәҶеҘідәәе’Ң管家пјҢдҪҶ他们д№Ӣй—ҙ并没жңүжҝҖзғҲзҡ„еҶІзӘҒдёҺд»ҮжҒЁпјҢжҷ®еёғзҡ„жҡҙеҠӣеҸӘжҳҜжқҘиҮӘдәҺд»–йқһзҗҶжҖ§зҡ„еҶІеҠЁпјӣгҖҠжӯ»дәЎзҡ„йўңиүІгҖӢдёӯе°јзҺӣе’ҢеӮ»еӯҗиҫҫеЁғжҳҜеҸҢиғһиғҺе…„ејҹпјҢдҪҶиҫҫеЁғзҡ„ж„ҸеӨ–жӯ»дәЎдҪҝе°јзҺӣж„ҹеҸ—еҲ°дәҶж·ұж·ұзҡ„жҮҠжӮ”дёҺеӯӨзӢ¬пјӣгҖҠеЎ”жҙӣгҖӢдёӯеЎ”жҙӣдёәеҠһзҗҶиә«д»ҪиҜҒжқҘеҲ°еҺҝеҹҺеҚҙиў«зҗҶеҸ‘йҰҶдёӯзҡ„зҹӯеҸ‘еҘіеӯ©йӘ—иө°дәҶжүҖжңүиҙўдә§е№¶еҮҸжҺүдәҶд»–ж Үеҝ—жҖ§зҡ„е°Ҹиҫ«еӯҗпјҢжңҖеҗҺеЎ”жҙӣеҸӘиғҪеӯӨзӢ¬ж— еҘҲең°йҮҚж–°еҠһзҗҶиҜҒ件照пјӣгҖҠз«ҷзқҖжү“зһҢзқЎзҡ„еҘіеӯ©гҖӢдёӯж— и®әжҳҜеҚ“зҺӣжӮІеҮүзҡ„е©ҡ姻пјҢиҝҳжҳҜд№ӢеҗҺеҘ№дёҺ“жҲ‘”д№Ӣй—ҙзҡ„з”ңиңңзҲұжғ…йғҪз”ұжҲ‘дёәеҘ№иҖғеӨ§еӯҰж—¶еҶҷдёӢзҡ„дёҖзҜҮдҪңж–ҮиҖҢиө·пјҢе°ҸиҜҙеңЁдёҖз§Қи·іи·ғжҖ§зҡ„еҸҷиҝ°ж—¶и·қе’ҢдёҖзі»еҲ—еҒ¶з„¶жҖ§жғ…иҠӮе®үжҺ’дёӯ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ҚеӯӨзӢ¬еҮ„еҮүж„ҹпјӣгҖҠи„‘жө·дёӯзҡ„дёӨдёӘдәәгҖӢдёӯ“з–Ҝе©Ҷеӯҗ”йҳҝеҰҲеҶ·жҺӘи„‘жө·йҮҢйҷӨдәҶиҮӘе·ұзҡ„з”·дәәе’Ңе„ҝеӯҗдёҚи®°еҫ—е…¶д»–д»»дҪ•дәӢжғ…пјҢдҪҶд»ҺеҘ№зҡ„еҜ№иҜқдёӯиҜ»иҖ…дәҰиғҪж„ҹеҸ—еҲ°йҳҝеҰҲеҶ·жҺӘеҶ…еҝғе……ж»Ўзҡ„жҒҗжғ§дёҺдјӨз—ӣпјӣгҖҠ第дёүе№ҙгҖӢи®Іиҝ°дәҶдёҖдҪҚдёӯе№ҙеҰҮеҘіеҜ»жүҫеғ§дәәдёәе·ІйҖқдё–дёүе№ҙзҡ„дәЎеӨ«еҝөз»Ҹи¶…еәҰзҡ„ж•…дәӢпјҢдҪҶе°ҸиҜҙдёӯз¬ҰеҸ·еҢ–зҡ„дәәзү©зјәд№ҸзӘҒеҮәзҡ„жҖ§ж јзү№еҫҒпјҢе‘ҲзҺ°еҮәе№ійқўеҢ–зҡ„еҸҷдәӢзү№еҫҒгҖӮз”ұжӯӨз§Қз§Қ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и®ёеӨҡе°ҸиҜҙдёӯдё»дәәе…¬зҡ„еҮәзҺ°гҖҒиЁҖиҜӯгҖҒдёҫеҠЁд»ҘеҸҠзү№ж®Ҡзҡ„ж„ҹзҹҘйғҪе»әз«ӢеңЁдёҖз§ҚеҒ¶з„¶жҖ§зҡ„жӮІеү§д№ӢдёҠпјҢиҖҢдәәзү©еҪўиұЎиғҢеҗҺе…іж¶үзҡ„д№ҹйғҪжҳҜдәәзү©еӨҚжқӮзҡ„еҶ…еҝғеӣҫејҸе’ҢйқһзҗҶжҖ§жғ…ж„ҹ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ӯӨзұ»е°ҸиҜҙдёӯжӮІеү§жІЎжңүеӨ§иө·еӨ§иҗҪзҡ„еҙҮй«ҳж„Ҹе‘іпјҢд№ҹзјәд№Ҹе®ҸеӨ§еҸҷдәӢзҡ„ж·ұеәҰпјҢжңүзҡ„еҸӘжҳҜж— еҠ©дәәзү©зҡ„еҒ¶з„¶жҖ§зҡ„дёҫеҠЁе’ҢеҚ‘еҫ®дәәзү©зҡ„еӨұиҙҘгҖҒжҢ«жҠҳгҖҒз„ҰзҒјдёҺеҮ„жҖҶпјҢиЎЁзҺ°зқҖдәәзү©ж— жі•ж‘Ҷи„ұзҡ„еҶ…еҝғзӘҳеўғ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ҡ“жҲ‘зҡ„е°ҸиҜҙеҸҜиғҪжӣҙжіЁйҮҚдёӘдәәеҢ–зҡ„дёңиҘҝпјҢзҺ°е®һйўҳжқҗзҡ„жҜ”иҫғе°‘пјҢеӨҡж•°жҳҜжҜ”иҫғиҷҡе№»зҡ„дёңиҘҝпјӣдҪҶжҳҜеңЁз”өеҪұйҮҢеҜ№ж°‘ж—ҸгҖҒеӨ§дј—зҡ„еӣ зҙ жҖқиҖғеҫ—дјҡзӣёеҜ№еӨҡдёҖдәӣпјҢеӣ иҖҢе°ұжҜ”иҫғе®һгҖӮеҶ…еҝғд№ӢдёӯжҲ‘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зәҜзІ№зҡ„еҶҷе®һдё»д№үиҖ…гҖӮ”[10]жӯӨеӨ„дҪңиҖ…жүҖжҢҮзҡ„“дёӘдәәеҢ–зҡ„дёңиҘҝ”е’Ң“иҷҡе№»зҡ„дёңиҘҝ”еҸҜд»Ҙиў«зңӢеҒҡжҳҜд»–дёӘдәәзҡ„иүәжңҜиҝҪжұӮгҖӮеңЁиҝ‘дёүеҚҒе№ҙзҡ„е°ҸиҜҙеҲӣдҪңдёӯпјҢжҲ‘们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ӣ еҸ—иҘҝж–№еҗҺзҺ°д»Јж–ҮеӯҰдёҺдёӯеӣҪеҪ“д»Је…Ҳй”Ӣж–ҮеӯҰзҡ„еҪұе“ҚпјҢе…¶е°ҸиҜҙ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д»Һдё»йўҳиЎЁиҫҫгҖҒеҸҷдәӢзӯ–з•ҘгҖҒиүәжңҜйЈҺж јзӯүеӨҡж–№йқўйғҪжҳҫзӨәеҮәдәҶеҗҺзҺ°д»Јдё»д№ү[11]зҡ„йЈҺж јзү№еҫҒгҖӮиҜёеҰӮпјҢиҚ’иҜһгҖҒйӯ”е№»гҖҒжҲҸд»ҝгҖҒжҡҙйңІеҸҷдәӢиҜқиҜӯзӯүзү№еҫҒеңЁд»–зҡ„е°ҸиҜҙдёӯжҳҜиҫғдёәжҳҺжҳҫзҡ„гҖӮеҪ“然пјҢиҝҷ并дёҚ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еҚ•еҗ‘жҺҘеҸ—зҡ„иҝҮзЁӢ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дёӘиһҚе…ҘдәҶиҮӘжҲ‘зҗҶи§ЈдёҺж„ҹжӮҹ并йҡҸзқҖдҪңиҖ…еҶҷдҪңз»ҸеҺҶзҡ„дё°еҜҢиҖҢеҸҳеҢ–зҡ„иҝҮзЁӢпјҢе…¶дёӯйҮҚж–°зҗҶи§Јжң¬еңҹж–ҮеҢ–иө„жәҗпјҢд»ҘжӯӨжҺўеҜ»дёҖз§Қжң¬еңҹзҡ„иЁҖиҜҙж–№ејҸе°ұжҳҜйҮҚиҰҒзү№зӮ№д№ӢдёҖгҖӮжҳҜд»Ҙ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пјҢе°Өе…¶жҳҜжӯҘе…ҘдәҢеҚҒдёҖдё–зәӘд№ӢеҗҺзҡ„е°ҸиҜҙжӣҙдёәзӘҒеҮәең°иЎЁзҺ°дәҶдҪңиҖ…зҡ„дёӘдәәзҗҶи§ЈдёҺеӨ–жқҘеҪұе“Қд№Ӣй—ҙжүҖеҪўжҲҗзҡ„дәӨжұҮиһҚеҗҲзү№еҫҒгҖӮ
дёүгҖҒж°‘ж—Ҹж–ҮеҢ–дёҺз”ҹжҙ»жң¬зңҹиүІеҪ©зҡ„дёҚеҗҢиЎЁиҝ°
ж–ҮеҢ–иә«д»Ҫеҝ…然дјҡдҪҝжҜҸдёӘж°‘ж—Ҹзҡ„дҪң家е°Ҷеҗ„иҮӘжүҖеұһж°‘ж—Ҹзҡ„ж–ҮеҢ–еӣ зҙ еј•е…Ҙе°ҸиҜҙеҲӣдҪңд№ӢдёӯпјҢд»ҘжӯӨеҪўжҲҗж–Үжң¬ж°‘ж—ҸеҢ–зҡ„зү№зӮ№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ҹжҳҜеҰӮжӯӨпјҢеңЁд»–зҡ„е°ҸиҜҙдёӯжҲ‘们дәҰиғҪеҸ‘зҺ°и®ёеӨҡеёҰжңүж–ҮеҢ–з¬Ұз ҒжҖ§зҡ„ж°‘ж—ҸеҢ–иЎЁиҝ°ејҸж ·пјҢиҖҢеңЁе°ҸиҜҙдёӯдҪңиҖ…еҸҲе°ҶиҝҷдёҖзү№зӮ№дёҺеҗҺзҺ°д»ЈеҸҷдәӢйЈҺж јзӣёиҝһпјҢдҪҝж–Үжң¬е…·еӨҮдәҶдёҖз§ҚдёҚеҗҢзҡ„е®ЎзҫҺе“Ғж јгҖӮеҰӮгҖҠиҜұжғ‘гҖӢдёҺгҖҠжІЎжңүдёӢйӣӘзҡ„еҶ¬еӨ©гҖӢдёӯдҪӣж•ҷзҡ„иҪ®еӣһи§ӮеҝөдёҺеӯӨзӢ¬иҷҡж— ж„ҹзҡ„дәӨиһҚпјӣгҖҠйҷҢз”ҹдәәгҖӢйҮҢ“дәҢеҚҒдёҖдёӘеҚ“зҺӣ”иҝҷдёҖи—Ҹдј дҪӣж•ҷж–ҮеҢ–з¬Ұз Ғе’Ңж–Үжң¬жүҖеұ•зҺ°зҡ„еҜ»жүҫдёҺзӯүеҫ…зҡ„еҫ’еҠізӯүйғҪдёәиҜ»иҖ…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з§ҚдёҚеҗҢзҡ„йҳ…иҜ»дҪ“йӘҢ[12]гҖӮеҶҚиҖ…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жңҹеҲӣдҪңдёӯеёҰжңүзҺ°е®һдё»д№үзү№еҫҒзҡ„йӮЈдәӣи—ҸиҜӯеҶҷдҪңжӣҙжҳҜдҪ“зҺ°дәҶдҪңиҖ…еҜ№ж°‘ж—Ҹж–ҮеҢ–дёҺзҺ°е®һз”ҹжҙ»зҡ„жҠҠжҸЎе§ҝжҖҒ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пјҢжһҒдёәйҮҚиҰҒзҡ„дёҖдёӘж–Үжң¬зү№еҫҒе°ұжҳҜеёҰзқҖйІңжҳҺзҡ„ж°‘й—ҙж•…дәӢгҖҒж°‘й—ҙдј иҜҙзҡ„зү№зӮ№гҖӮжҚўеҸҘиҜқиҜҙпјҢд»–зҡ„и®ёеӨҡе°ҸиҜҙйҖүжӢ©зҡ„ж•…дәӢзұ»еһӢгҖҒеӨ„зҗҶж•…дәӢзҡ„ж–№ејҸгҖҒиҗҘйҖ зҡ„ж°ӣеӣҙгҖҒйӮЈз§ҚзӢ¬зү№иҖҢеқҰиҜҡзҡ„и®Іж•…дәӢзҡ„и…”и°ғгҖҒз»“жһ„пјҢз»ҹз»ҹйғҪеёҰзқҖж°‘й—ҙж•…дәӢгҖҒж°‘й—ҙдј иҜҙзү№жңүзҡ„еЈ°и°ғгҖӮ”[13]е°ҸиҜҙгҖҠе°ёиҜӯж–°иҜҙпјҡжһӘгҖӢдҝқз•ҷдәҶ“еүҚж–Үжң¬”гҖҠе°ёиҜӯж•…дәӢгҖӢзҡ„еҸҷдәӢеҪўејҸ并еҠ д»ҘйҮҚз»„пјҢд»Ҙ“ж•…дәӢж–°зј–”зҡ„ж–№ејҸйҮҚзӯ‘дәҶж–°зҡ„е®ЎзҫҺз©әй—ҙпјӣгҖҠеҜ»жүҫжҷәзҫҺжӣҙзҷ»гҖӢдёӯеҲҶж•ЈејҸең°йҮҚиҝ°дәҶи—ҸжҲҸеү§жң¬гҖҠжҷәзҫҺжӣҙзҷ»гҖӢзҡ„ж•…дәӢпјҢиҝҷдәӣйғҪжһ„жҲҗдәҶж–Үжң¬д№Ӣй—ҙзҡ„дә’ж–ҮжҖ§е…ізі»пјҢиҖҢжӯӨеүҚжүҖиҜҙз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Ҝ№дәҺйӯ”е№»еҸҷдәӢзҡ„зҗҶи§ЈдёҺиҝҗз”ЁеңЁдёҖе®ҡж„Ҹд№үдёҠд№ҹеҪ°жҳҫдәҶд»–еҜ№ж°‘ж—Ҹж°‘й—ҙж–ҮеӯҰиө„жәҗзҡ„жҺўеҜ»гҖӮжӯӨеӨ–пјҢж°‘й—ҙж–Үжң¬дёӯйҮҚеӨҚзҡ„еҸҷиҝ°зү№зӮ№еҸҠе…¶жүҖе‘ҲзҺ°зҡ„еңҶеҪўжЁЎејҸд№ҹйў‘з№Ғең°еҮәзҺ°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и®ёеӨҡе°ҸиҜҙдёӯпјҢеҰӮгҖҠиҜұжғ‘гҖӢгҖҠжҷ®еёғгҖӢгҖҠеҚҲеҗҺгҖӢдёӯдё»дәәе…¬зҡ„еҠЁдҪңйҮҚеӨҚпјӣгҖҠжөҒжөӘжӯҢжүӢзҡ„жўҰгҖӢдёӯж¬Ўд»Ғе’ҢгҖҠ第д№қдёӘз”·дәәгҖӢдёӯйӣҚжҺӘзҡ„иҜқиҜӯйҮҚеӨҚ[14]пјӣгҖҠеҜ»и®ҝйҳҝеҚЎеӣҫе·ҙгҖӢдёӯеҜ№дё»дәәе…¬йҳҝеҚЎеӣҫе·ҙеҪўиұЎзҡ„дёҚж–ӯи§Јжһ„дёҺйҮҚеЎ‘зӯүзқҖе®һејәеҢ–дәҶж–Үжң¬зҡ„дё»йўҳжҢҮеҗ‘гҖӮжӯӨеӨ–пјҢеҜ»жүҫдёҚд»…жҳ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дёӯ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ҜҚйўҳпјҢд№ҹжҳҜдёҖз§ҚеҜ№ж°‘ж—Ҹж–ҮеҢ–зҡ„и§Ӯз…§е’ҢеҜ№ж°‘ж—Ҹж–ҮеҢ–еӨҡе…ғиЎЁиҝ°ж–№ејҸзҡ„жҺўеҜ»гҖӮеҰӮгҖҠеҜ»и®ҝйҳҝеҚЎеӣҫе·ҙгҖӢйҖҡиҝҮи®Іиҝ°дёҖеҲҷж°‘й—ҙиүәдәәзҡ„ж•…дәӢе‘ҲзҺ°дәҶдҪңиҖ…еҜ№ж°‘ж—Ҹж°‘й—ҙж–ҮеҢ–зҡ„е…іеҲҮпјӣгҖҠеҜ»жүҫжҷәзҫҺжӣҙзҷ»гҖӢдёӯеҜ»жүҫ“жҷәзҫҺжӣҙзҷ»”зҡ„жј”е‘ҳд№ҹеҗҢж ·еұ•йңІдәҶдҪңиҖ…еҜ№зҺ°д»ЈжҖ§еҶІеҮ»дёӢи—Ҹж–ҮеҢ–зҡ„е®Ҳжңӣе§ҝжҖҒ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жңҹе°ҸиҜҙеҲӣдҪңдёӯдёҚд№ҸеҜ№еҗҺзҺ°д»ЈеҸҷдәӢжҠҖе·§ж–№йқўзҡ„еҖҹйүҙпјҢд»ҺдёӯеҸҜеҜ»и§…еҮәжҳҺжҳҫзҡ„еҗҺзҺ°д»Јдё»д№үз—•иҝ№гҖӮ然иҖҢпјҢд»Һиҝ‘е№ҙжқҘзҡ„е°ҸиҜҙеҲӣдҪңжқҘзңӢпјҢжҲ‘们д№ҹиғҪеҸ‘зҺ°е…¶еҶҷдҪңжӯЈеңЁж…ўж…ўеҸ‘з”ҹзқҖеҸҳеҢ–пјҢеҚіејҖе§ӢеҒҸзҰ»еҺҹе…ҲйӮЈз§ҚйҮҚ“жҠҖе·§жҖ§”зҡ„зҫҺеӯҰйЈҺж јпјҢиҖҢд»Ҙд№ҰеҶҷи—ҸеҢәз”ҹжҙ»жң¬зңҹиүІеҪ©пјҢеӣһеҪ’ж—ҘеёёзҺ°е®һзҡ„еҶҷе®һе§ҝжҖҒеҗ‘еүҚиҝҲиҝӣ并еҠӘеҠӣе»әз«ӢдёҖз§ҚдёҺжӯӨеүҚдёҚеҗҢзҡ„з®ҖзәҰжҖ§еҸҷиҝ°йЈҺж јзҡ„е°қиҜ•пјҢиҖҢиҝҷеҸҲдёҺж–Үжң¬дёӯеҪұеғҸеҢ–зҡ„иЎЁиҫҫж–№ејҸ[15]зӣёз»“еҗҲжҸҸж‘№дәҶи—Ҹең°иҫ№зјҳе°Ҹдәәзү©зҡ„з”ҹжҙ»зҠ¶жҖҒдёҺжғ…ж„ҹдё–з•ҢгҖӮеңЁдёӯеӣҪеҪ“д»Јж–ҮеӯҰзҡ„иҜӯеўғдёӯпјҢеҜ№и—ҸеҢәзҡ„д№ҰеҶҷдёҖзӣҙеӯҳеңЁзқҖдёҖз§ҚжғіеғҸжҖ§зҡ„д»–иҖ…и§ҶйҮҺпјҢиҮҙдҪҝеңЁзӣёеҪ“зЁӢеәҰдёҠйҒ®и”ҪдәҶи—ҸеҢәзҡ„зңҹе®һеӨ„еўғгҖӮеҪ“дёӢи®ёеӨҡеҲӣдҪңиҖ…еңЁејҖе§ӢеҸҚжҖқжӯӨз§ҚеҶҷдҪңж–№ејҸ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ҹжҳҜе…¶дёӯдёҖдҪҚпјҢд»–еҜ№жӯӨиҝӣиЎҢдәҶж·ұеҲ»еҸҚжҖқпјҢеҠӘеҠӣд№ҰеҶҷзқҖи—ҸеҢәжң¬зңҹз”ҹжҙ»зҡ„жғ…зҠ¶пјҢ然иҖҢпјҢжӯӨз§ҚйҮҚеӣһеҶҷе®һзҡ„е§ҝжҖҒжҳҫ然дёҚеҗҢдёҺдј з»ҹж„Ҹд№үдёҠзҡ„зҺ°е®һдё»д№ү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з§Қзі…еҗҲдәҶдёӘдәәеҗҺзҺ°д»ЈзҗҶеҝөзҡ„зҺ°е®һдё»д№үгҖӮд№ҹжӯЈеӣ еҰӮжӯӨпјҢжһҒз®Җдё»д№ү[16]ејҸзҡ„еҶҷдҪңзӯ–з•ҘжҒ°жҒ°дёәд»–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з§ҚиЎЁиҝ°зҺ°е®һзҡ„ж°‘ж—Ҹз”ҹжҙ»дёҺж°‘ж—Ҹж–ҮеҢ–зҡ„дёҚеҗҢж–№ејҸгҖӮеҰӮпјҢгҖҠиҚүеҺҹгҖӢжүҖдҪ“зҺ°еҮәзҡ„“дҪӣж•ҷж…ҲжӮІдёҺдј з»ҹеҲ‘жі•д№Ӣй—ҙеӯҳеңЁзҡ„еј еҠӣе’ҢеҶ…еҝғеҶІзӘҒ”[17]д»ҘеҸҠеә•еұӮдәәзү©зҡ„дјҰзҗҶж„ҸиҜҶпјӣгҖҠеҳӣе‘ўзҹігҖҒ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еҳӣе‘ўзҹідәәдёҺдё»дәәе…¬жҙӣжЎ‘д№Ӣй—ҙжўҰдёӯеҜ№иҜқжүҖиЎЁзҺ°зҡ„дәәзү©жҖқз»ҙдёҺж•…дәӢзҡ„зүҮж®өжҖ§з»“жһ„пјӣгҖҠиүәжңҜ家гҖӢдёӯе°Ҹе–Үеҳӣе’ҢиҖҒе–Үеҳӣд»ҘеҸҠеҮ дёӘеӨ–ең°дәәд№Ӣй—ҙзҡ„еҜ№иҜқжүҖжһ„зӯ‘зҡ„жңқеңЈиҖ…зҡ„еҶ…еҝғдё–з•ҢдёҺдәәзү©еҪўиұЎзҡ„е№ійқўеҢ–пјӣгҖҠй»„жҳҸ·е…«е»“иЎ—гҖӢйҮҢеӯ©з«ҘеӨ©зңҹзҡ„зҗҶи§ЈеҸҠзҺ°д»ЈдёҺдј з»ҹд№Ӣй—ҙзҡ„еӨҡйҮҚе…ізі»пјӣгҖҠеЎ”жҙӣгҖӢдёӯзҺ°д»Ји—Ҹдәәзҡ„иә«д»Ҫи®ӨеҗҢдёҺе°ҸиҜҙзҡ„иҗ§з–Ҹж„Ҹе‘іпјӣгҖҠж’һжӯ»дәҶдёҖеҸӘзҫҠгҖӢдёӯз”ұдё»дәәе…¬жүҖиЎЁиҫҫзҡ„йҒ“еҫ·дјҰзҗҶд»ҘеҸҠе°ҸиҜҙз®ҖжҳҺзҡ„еҸҷдәӢйЈҺж јпјӣгҖҠж°”зҗғгҖӢйҮҢзӨҫдјҡеҸҳиҝҒдёҺдҪӣж•ҷиҪ®еӣһзҡ„з”ҹе‘Ҫи§ӮеҝөеңЁдәәзү©иә«дёҠдҪ“зҺ°еҸҠе…¶иҪ»жҳ“зҡ„ж•…дәӢжғ…иҠӮпјӣгҖҠиөӨи„ҡеҢ»з”ҹгҖӢдёӯеә•еұӮдәәзү©зҡ„жғ…ж„ҹеҺҶзЁӢе’ҢдәәжҖ§е–„д№ӢдјҰзҗҶиҜүжұӮдёҺж•…дәӢжғ…иҠӮдёӯзҡ„еӨҡз§ҚеҒ¶з„¶жҖ§зӯүиҜёеӨҡж–№йқўж—ўеҪ°жҳҫдәҶдёҮзҺӣжүҚж—ҰдёҖз§ҚеҺ»д»–иҖ…еҢ–зҡ„д№ҰеҶҷзӯ–з•Ҙе’ҢйҮҚеӣһзҺ°е®һзҡ„еҶҷдҪңе§ҝжҖҒпјҢеҸҲдҪ“зҺ°дәҶдёҚеҗҢдёҺдј з»ҹзҺ°е®һдё»д№үзҡ„еҶҷе®һзү№зӮ№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ҡ“жҲ‘笔дёӢзҡ„и—Ҹең°еҸҜиғҪжӣҙж—ҘеёёпјҢжӣҙдё–дҝ—пјҢдҪ йҖҡиҝҮжҲ‘зҡ„ж–Үеӯ—жҲ–еҪұеғҸпјҢдҪ дјҡи§үеҫ—дҪңдёәдәәпјҢжң¬иҙЁдёҠе’ҢдҪ 们д№ҹжІЎжңүеӨҡеӨ§еҢәеҲ«гҖӮжҲ‘еҸҜиғҪжӣҙдәҶ解他们дҪңдёәдәәзҡ„жңҖз»Ҷеҫ®зҡ„жғ…ж„ҹж–№ејҸгҖӮ”[18]з”ұжӯӨпјҢжҲ‘们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дҪңиҖ…д»ҘдёҖз§Қжҷ®йҒҚдәәжҖ§зҡ„з»ҙеәҰд№ҰеҶҷдәәзү©зҡ„з”ҹеӯҳж„ҹжӮҹдёҺеҶ…еҝғдё–з•Ң[19]пјҢеңЁеҺ»йҷӨдәҶдәәзү©иә«дёҠиў«еӨ–йғЁдё–з•ҢејәеҠ зҡ„ж ҮзӯҫеҗҺе‘ҲзҺ°еҮәдәҶз”ҹжҙ»зҡ„жң¬иҙЁиүІеҪ©пјҢиҖҢжӯӨзұ»йЈҺж је»әз«ӢеңЁж—Ҙеёёз”ҹжҙ»з»ҶиҠӮзҡ„жһ„зӯ‘д№ӢдёҠпјҢжҳҜдёҖз§Қз”ҹжҙ»зҫҺеӯҰзҡ„дҪ“зҺ°пјҢе°ҸиҜҙжүҖеҢ…еҗ«зҡ„е®—ж•ҷзҡ„гҖҒж°‘дҝ—зҡ„гҖҒйҒ“еҫ·зҡ„еӨҡйҮҚж„Ҹи•ҙзҡ„иЎЁиҝ°д№ҹеңЁиҝҷз§ҚзҫҺеӯҰйЈҺж јдёӯзӘҒеҮәдәҶзү№е®ҡж–ҮеҢ–еҝғзҗҶдёӢзҡ„иҫ№зјҳе°Ҹдәәзү©зҡ„жң¬зңҹз”ҹжҙ»еӨ„еўғдёҺзІҫзҘһдё–з•ҢгҖӮ
еңЁжӯӨеҖјеҫ—дёҖжҸҗзҡ„жҳҜ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и®ёеӨҡе°ҸиҜҙд»Ҙе„ҝз«Ҙи§Ҷи§’еұ•ејҖ[20]пјҢдёәж–Үжң¬е»әжһ„дәҶдёҖз§ҚзәҜжғ…з®ҖжҳҺгҖҒеӨ©зңҹжҙ»жіўзҡ„иүәжңҜйЈҺж јпјҢд»Һе„ҝз«ҘиҙЁжңҙзҡ„дҪ“йӘҢж„ҹеҸ—дёӯжӣҙдёәйІңжҳҺең°жҠҳе°„еҮәдәҶд»–жүҖжҸҸз»ҳзҡ„з”ҹеӯҳдё–з•Ңзҡ„жң¬зңҹиүІеҪ©гҖӮгҖҠй»Ҝж·Ўзҡ„еӨ•йҳігҖӢдёӯе°ҸеҘіеӯ©еҜ№жҜҚдәІзҡ„жҖқеҝөпјӣгҖҠе…«еҸӘзҫҠгҖӢдёӯз”ІжҙӣдёҺзҫҺеӣҪжёёе®ўзҡ„дәӨи°Ҳд»ҘеҸҠ他们еҶ…еҝғзҡ„еӯӨзӢ¬е’ҢзңҹиҜҡпјӣгҖҠдёҖеқ—зәўеёғгҖӢдёӯд№ҢйҮ‘жҙ»жіјеҸҜзҲұзҡ„еӯ©з«ҘжҖ§ж јдёҺеҘҪеҘҮзЁҡж°”зҡ„жҖқз»ҙж–№ејҸпјӣгҖҠжҲ‘жғіжңүдёӘе°ҸејҹејҹгҖӢдёӯдё№еўһеӨ©зңҹзғӮжј«е°‘е°Ҹж— зҢңзҡ„еҶ…еҝғдё–з•ҢдёҺд»–еҜ№ж–°з”ҹе‘Ҫзҡ„жңҹеҫ…пјӣгҖҠиүәжңҜ家гҖӢдёӯе°Ҹе–ҮеҳӣдёҺеҮ дёӘиЎҢдёәиүәжңҜ家д№Ӣй—ҙзҡ„еҜ№иҜқжүҖеұ•зҺ°зҡ„еӨ©зңҹпјӣгҖҠй»„жҳҸ·её•е»“иЎ—гҖӢдёӯе°Ҹз”·еӯ©дёҺдёӯе№ҙз”·еӯҗгҖҒиҖҒеҘ¶еҘ¶д№Ӣй—ҙзҡ„еҜ№иҜқжүҖеҗҗйңІзҡ„еӯ©з«ҘйЎҪзҡ®жҖ§ж јпјӣгҖҠж°”зҗғгҖӢдёӯеӯ©еӯҗ们еҜ№еӨ–йғЁдё–з•Ңзҡ„зәҜзңҹи®ӨзҹҘдёҺзӘҒеҸ‘зҡ„еҘҮжҖқеҰҷжғіпјӣгҖҠиөӨи„ҡеҢ»з”ҹгҖӢдёӯе°Ҹеӯ©е„ҝеҜ№жҲҗдәәдё–з•Ңзҡ„иҢ«з„¶дёҺе№Ҫй»ҳйЈҺи¶ЈзӯүйғҪд»Ҙе„ҝз«ҘеҸҷдәӢи§Ҷи§’еұ•ејҖдҪ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дёӯзҡ„дәәжҖ§з»ҙеәҰе’Ңз”ҹжҙ»жң¬зңҹиүІеҪ©жӣҙдёәйІңжҳҺгҖӮдҪңдёәеҸҷдәӢж–Үзұ»пјҢе°ҸиҜҙдёӯзҡ„еҸҷиҝ°дёҺи§Ҷи§’зҡ„йҖүжӢ©еҜҶдёҚеҸҜеҲҶпјҢиҖҢд»»дҪ•еҸҷдәӢи§Ҷи§’зҡ„йҖүжӢ©йғҪжҳҜдёҖз§ҚеҸҷдәӢзӯ–з•ҘпјҢеҚідҪңиҖ…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иҝҷдёӯзӯ–з•ҘиҫҫеҲ°жҹҗз§ҚеҸҷдәӢж•ҲжһңгҖӮеңЁе°ҸиҜҙдёӯж— и®әжҳҜиЁҖиҜҙиҖ…иҝҳжҳҜи§ӮзңӢиҖ…пјҢе…¶еҜ№ж–Үжң¬йЈҺж јзҡ„жһ„зӯ‘йғҪе…·йҮҚиҰҒдҪңз”ЁгҖӮе„ҝз«Ҙз”ұдәҺиҫғе°‘еҸ—зӨҫдјҡж–ҮеҢ–ж„ҸиҜҶжөёжҹ“еҸҠ他们зӣҙи§үжҖ§зҡ„ж„ҹжҖ§зҡ„е’ҢдёҚжҲҗзҶҹзҡ„жҠҪиұЎжҖқз»ҙзӯүеӣ зҙ дҪҝ他们еҸӘиғҪи§ӮеҜҹеӨ–йғЁдё–з•Ңзҡ„иЎЁиұЎпјҢж— жі•жҺҢжҸЎжӣҙдёәйҡҗз§ҳзҡ„ж·ұеұӮзҡ„ж„Ҹд№ү并еҒҡеҮәжҳҜйқһеҲӨж–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Үжң¬дёӯзҡ„е„ҝз«Ҙи§Ҷи§’е°ұд»Ҙе„ҝз«Ҙзү№жңүзҡ„ж„ҹеҸ—еҪўејҸгҖҒжҖқз»ҙж–№ејҸгҖҒиҜӯиЁҖеҸҘејҸй“әеҶҷеӨ–еңЁдё–з•ҢпјҢеӣ иҖҢзӣёеҪ“зЁӢеәҰдёҠеүҘзҰ»дәҶжҲҗдәәдё–з•Ңзҡ„иҷҡдјӘе’ҢеҒҮиұЎ[21]пјҢеұ•зӨәеҮәдәҶдёҖе№…з”ҹеӯҳдё–з•Ңзҡ„жң¬еҺҹд№Ӣзӣё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зәөи§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дёүеҚҒе№ҙзҡ„еҶҷдҪңеҺҶзЁӢпјҢе…¶дёӯдёҖдёӘиҫғдёәйҮҚиҰҒзҡ„зү№еҫҒе°ұжҳҜд»ҘдёҖз§Қжң¬еңҹи§ҶйҮҺе…іжіЁеҗҢиҙЁжҖ§дёҺйҮҚеӨҚжҖ§зҡ„зҗҗзўҺзҡ„ж—Ҙеёёз”ҹжҙ»иҝӣиҖҢеҸҷиҜҙи—Ҹең°з”ҹжҙ»зҡ„жң¬зңҹиүІеҪ©зҡ„еҶҷдҪңиҪ¬еҗ‘гҖӮ
з»“иҜӯ
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дёӯеӯҳеңЁзқҖжҜҚиҜӯгҖҒжұүиҜӯгҖҒ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зӯүеҶҷдҪңзҺ°иұЎпјҢиҝҷд»ҺдёҖдёӘдҫ§йқўеұ•зҺ°дәҶ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зҡ„дё°еҜҢжҖ§е’ҢеӨҚжқӮжҖ§пјҢиҖҢиҝҷдёҚд»…д»…е…іж¶үеҲ°иҜӯиЁҖеұӮйқўпјҢд№ҹж¶үеҸҠзӨҫдјҡж–ҮеҢ–еұӮйқўпјҢеӣ жӯӨпјҢиөӢдәҲдәҶжҺҘеҸ—иҖ…еҫҲеӨ§зҡ„йҳҗйҮҠз©әй—ҙгҖӮе°ұи—Ҹж—ҸеҪ“д»Јж–ҮеӯҰдёӯзҡ„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зҺ°иұЎиҖҢиЁҖпјҢд»ҺдҪңиҖ…еұӮйқўпјҢ他们еҖҹеҠ©дёӨз§ҚиҜӯиЁҖиЎЁиҝ°зқҖиҮӘе·ұзҡ„иүәжңҜж—Ёи¶ЈпјҢе…¶дёӯж¶үеҸҠдҪңиҖ…зҡ„еҶҷдҪңз«Ӣеңәе’ҢиҜӯиЁҖйҖүжӢ©зӯ–з•ҘпјҢд№ҹж¶үеҸҠи·ЁиҜӯйҷ…зҡ„дј ж’ӯж–№ејҸгҖӮд»ҺиҜ»иҖ…еұӮйқўиҖҢиЁҖпјҢ他们дҫқжҚ®дёҚеҗҢзҡ„иҜӯиЁҖеҪўжҖҒиҺ·еҸ–дёҚеҗҢзҡ„е®ЎзҫҺзҗҶи§ЈпјҢеҸҲжӣҙе…·дёҚеҗҢзҡ„ж–ҮеҢ–иҜӯеўғжқҘзҗҶи§Је’ҢйҳҗйҮҠпјҢд»ҘжӯӨжһ„жҲҗдәҶж—ўиҒ”зі»еҸҲдёҚзӣёеҗҢзҡ„жҺҘеҸ—и§ҶйҮҺгҖӮеңЁи—Ҹж—ҸеҪ“д»ЈеҸҢиҜӯдҪң家зҫӨдёӯ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Ҙ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е’ҢиҮӘиҜ‘зӯ–з•Ҙжһ„зӯ‘дәҶеҗҢдёҖж–Үжң¬зҡ„дёҚеҗҢе®ЎзҫҺжҺҘеҸ—з»ҙеәҰпјҢз”ұжӯӨд№ҹеҪўжҲҗдәҶеҸҢиҜӯж–Үжң¬д№Ӣй—ҙзҡ„дә’иЎҘ并еӯҳе…ізі»пјҢиҖҢеңЁеҸҢиҜӯеҲӣдҪңдёӯд»–еҸҲе°Ҷжң¬еңҹиө„жәҗдёҺеӨ–жқҘеӣ зҙ иһҚдёәдёҖдҪ“дҪҝе…¶е°ҸиҜҙе…·еӨҮдәҶж°‘ж—ҸжҖ§дёҺзҺ°д»ЈжҖ§зӣёе…јзҡ„еӨҡз»ҙе“Ғж јгҖӮе°Өе…¶иҝ‘е№ҙжқҘ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еҲӣдҪңеңЁе…јйЎҫдёӘжҖ§еҢ–зҡ„иүәжңҜиЎЁиҫҫзҡ„еҗҢж—¶пјҢиҜ•еӣҫеңЁдёҖз§ҚеҺ»д»–иҖ…еҢ–зҡ„еҶҷдҪңдёӯд»Ҙжң¬еңҹи§Ҷи§’жқҘи§Ӯз…§и—ҸеҢәз”ҹжҙ»зҡ„зңҹе®һпјҢз”ЁдёҖз§Қз®ҖзәҰеҢ–зҡ„иҜқиҜӯиЎЁиҫҫзқҖд»–еҜ№жң¬зңҹз”ҹжҙ»зҡ„ж„ҹжӮҹдёҺзҗҶи§Ј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дёӯзҺ°д»ЈдёҺдј з»ҹгҖҒзҘһз§ҳдёҺе№іеҮЎгҖҒжң¬еңҹдёҺеӨ–жқҘзӯүе…ғзҙ зі…еҗҲеңЁдёҖиө·пјҢе…ұеҗҢиҗҘйҖ дәҶе…¶е°ҸиҜҙзӢ¬зү№зҡ„иүәжңҜйӯ…еҠӣгҖӮ
гҖҗеҸӮиҖғж–ҮзҢ®гҖ‘
[1]з«ҘеәҶзӮіпјҡж–ҮеӯҰиҜӯиЁҖи®ә[J]пјҢеӯҰд№ дёҺжҺўзҙў,1999(3):104.
[2]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е°ҸиҜҙеҶҷдҪңжҳҜжҲ‘еҶ…еҝғзҡ„йңҖиҰҒ[N]пјҢиҘҝжө·йғҪеёӮжҠҘ,2014е№ҙ7жңҲ7ж—Ҙ:A26.
[3]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зңҹжӯЈеҝғзҒөзҡ„еӣһеҪ’еҫҲйҡҫ[EB/OL]пјҢhttps://news.163.com/14/0622/14/9VBO5LM500014AED.htmlпјҢ2014-06-22/2018-04-03
[4]жңқжҲҲйҮ‘пјҡдёӯеӣҪеҸҢиҜӯж–ҮеӯҰпјҡзҺ°зҠ¶дёҺеүҚжҷҜзҡ„зҗҶи®әжҖқиҖғ[J]пјҢж°‘ж—Ҹж–ҮеӯҰз ”з©¶,1991(1):17.
[5][7][10]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жқҺйҹ§пјҡйқҷйқҷзҡ„еҳӣе‘ўзҹі——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и°Ҳ[J]пјҢз”өеҪұиүәжңҜ,2006(1):32.
[6]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и—Ҹдәә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ж–ҮеӯҰдё–з•Ң[N]пјҢжҪҮж№ҳжҷЁжҠҘпјҢ2014е№ҙ4жңҲ21ж—ҘпјҡA16.
[8]е”җзәўжў…пјҢзҺӢе№іпјҡе®Ғйқҷдёӯзҡ„иҮӘдҝЎдёҺдјҳйӣ…——и®ә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еҲӣдҪңзҡ„зү№иүІдёҺж„Ҹд№ү[J]пјҢдёӯеҚ—ж°‘ж—ҸеӨ§еӯҰеӯҰжҠҘ,2014(6):159.
[9]еҚ“зҺӣпјҡдёӯеӨ–жҜ”иҫғи§ҶйҳҲдёӢзҡ„еҪ“д»ЈиҘҝи—Ҹж–ҮеӯҰ[M]пјҢдёҠжө·пјҡдёҠжө·еӨ§еӯҰеҮәзүҲзӨҫпјҢ2015:141.
[11] [зҫҺ]M.H.иүҫеёғжӢүе§Ҷж–Ҝпјҡж–ҮеӯҰжңҜиҜӯиҜҚе…ё[M]пјҢеҢ—дә¬пјҡеҢ—дә¬еӨ§еӯҰеҮәзүҲзӨҫпјҢ2009:336—339.
[12]йҫҷд»Ғйқ’пјҡж°‘й—ҙеҸҷдәӢиғҢжҷҜдёӢзҡ„ж–ҮеӯҰиүәжңҜиҜүжұӮпјҡдёҖз§Қд№ҰеҶҷ“дҪӣз»Ҹ”иҲ¬зҡ„еҶІеҠЁпј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з”өеҪұгҖҒе°ҸиҜҙеҸҠзҝ»иҜ‘[J]пјҢдёңеҗҙеӯҰжңҜ,2015(4):65.
[13]马钧пјҡйЈҺйӣӘеӨңеҪ’дәәеҰӮжҳҜиҜ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дё–з•Ң[J]пјҢйқ’жө·ж№–,2014(9):89.
[14]жқЁж…§д»Әпј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Ҝ“иЁҖејҸе°ҸиҜҙ——еңЁж·ұеұӮж„ҸиҜҶеҜ№зІҫзҘһзҠ¶жҖҒзҡ„еҸҷиҝ°[J]пјҢдёңеҗҙеӯҰжңҜ,2015(4):42.
[15]еҫҗжҷ“дёңпјҡйҒҮи§ҒдёҮзҺӣжүҚж—Ұ[M]пјҢжқӯе·һпјҡдёӯеӣҪзҫҺжңҜеӯҰйҷўеҮәзүҲзӨҫпјҢ2017:260.
[16]иҷһе»әеҚҺпјҡжһҒз®Җдё»д№ү[A]пјҢи§ҒйҮ‘иҺүгҖҒжқҺй“Ғдё»зј–пјҡиҘҝж–№ж–Үи®әе…ій”®иҜҚ.第дәҢеҚ·[C]пјҢеҢ—дә¬пјҡеӨ–иҜӯж•ҷеӯҰдёҺз ”з©¶еҮәзүҲзӨҫпјҢ2017:217—218.
[17]йғҒдё№гҖҒеҲҳеҶ¬жў…пј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з”өеҪұдёӯзҡ„дҪӣж•ҷжҷҜи§Ӯ[J]пјҢдёӯеӣҪи—ҸеӯҰ,2017(1):174.
[18]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дҪ•е№іпјҡи®ҝи°Ҳ“他们е°ұжҳҜйӮЈж ·зңҹе®һең°з”ҹжҙ»зқҖ”[J]пјҢиҠұеҹҺ,2017(1):110.
[19]йҹ©жҳҘиҗҚпјҡи®ә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зҡ„“ж„ҸиұЎеҜ№иҜқ”дёҺиҜ—жҖ§жҖқз»ҙ[J]пјҢиҘҝеҢ—ж°‘ж—ҸеӨ§еӯҰеӯҰжҠҘ,2015(5):174.
[20]жқҺзҫҺиҗҚпјҡзҺ°д»ЈиҜӯеўғдёӯи—Ҹж—Ҹж–ҮеҢ–еҸ‘еұ•жҺўеҫ®пјҡд»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ҲӣдҪңдёәдҫӢ[J]пјҢиҘҝи—Ҹж°‘ж—ҸеӨ§еӯҰеӯҰжҠҘ,2017(5):121.
[21]зҺӢй»Һеҗӣпјҡе„ҝз«Ҙи§Ҷи§’зҡ„еҸҷдәӢеӯҰж„Ҹд№ү[J]пјҢз»Қе…ҙж–ҮзҗҶеӯҰйҷўеӯҰжҠҘ,2004(2):52.
еҺҹеҲҠдәҺгҖҠиҘҝи—Ҹз ”з©¶гҖӢ2018е№ҙ第6жң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