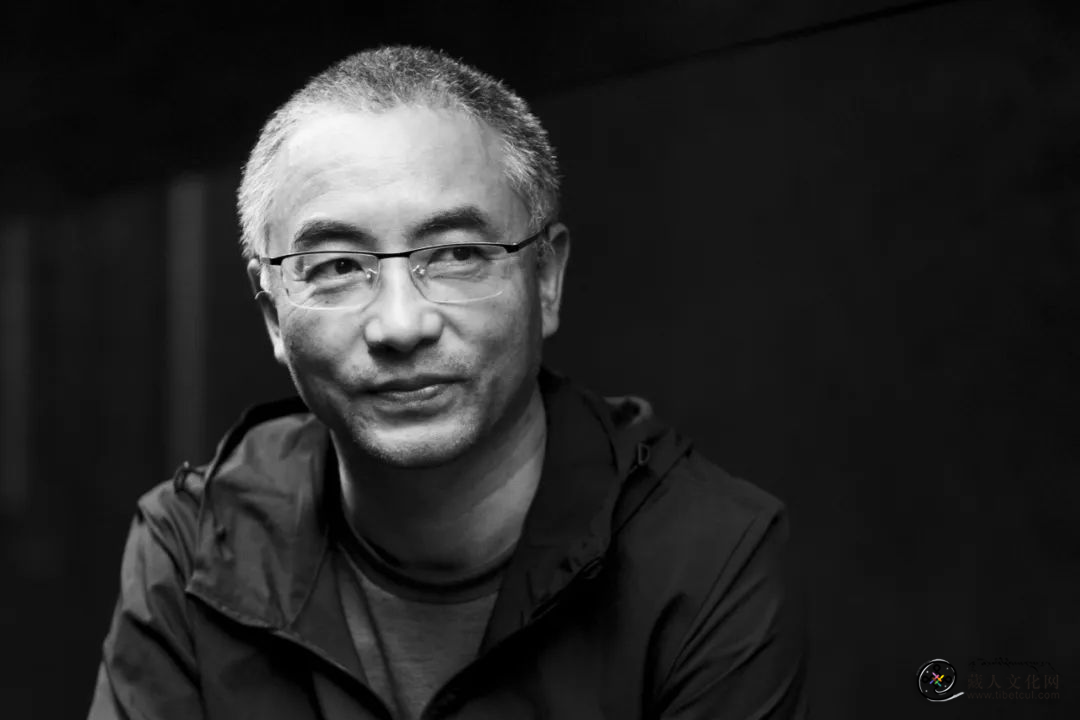诗人黎正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牧狼人》正式出版了,这部鲜活的藏文化题材的作品,除了精彩故事令人手不释卷,其稀有题材的罕见表达方式,也令人深深被震撼,半个月来都一直在回味儿。
一切因为一个神秘的名字——卓玛。
在雪域高原,卓玛是藏族女孩子喜欢使用的美丽名字,那里的少女们,即使父母没用这两个字取名,自己也愿意另外用一个带“卓玛”昵称面对世人,来寄托自己一生美好意愿。这是为什么呢?阅读完《牧狼人》,这个现象深厚的文化和人性的秘密,也许,就有了某种答案。
一、稀有的缘起设计
故事缘起是牧羊人扎西家的一场灭顶之灾,与其他灾难不同的是,这一场灾难是一群土匪和一群草原狼在同一个时间共同发动和造就的。土匪黄大郎抢走了扎西的妻子“卓玛”和女儿“梅朵”,而“乌岗狼王”率领的狼群,则把扎西家的羊群全部赶到了狼群储藏食物的冰湖里。更加不幸的是,土匪把他的女儿仍在草地直接就被狼群祸害了,这一瞬间来自人类和畜生们共同制造的灾祸,注定了故事的发展,是要跨越人群和狼群两界,并在人与兽之间纠缠。这种故事的设计,观察古今中外的小说,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就算前些年的畅销小说《狼图腾》的缘起设计,跟《牧狼人》相比,虽然故事也横跨“人与狼”两界,但其故事的紧张与面对的生死痛苦难题,跟这个相比,就单薄得多,小说的画面感和故事层次的丰富性,《牧狼人》这部小说,堪称“稀有”
二、怪异志与英雄赞的双螺旋结构
开篇的不同凡响,小说的内容和结构注定有别出心裁的表达。在我读来,这个藏区打箭麓的若拉草原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神话时代向英雄时代过渡的特殊王国。人类世俗生活与某种神性生活相辅相成:一方面是狼群、天葬秃鹰、藏獒、三尾红狐等颇具灵性的动物,分别于牛羊生存、肉身与灵魂取舍、牧人伴侣、祸福吉凶等发生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这种天人互动又互相干扰角力的画面,颇像古代《山海经》《搜神记》对于人与神的理解和表达;其中有个神秘的细节是,乌岗狼王每次受伤以后,都能够在神奇的山洞的石碟上疗伤,重新聚集能量,从头再来,这些故事,像极了神与人类共同存在“神话时代”;另一方面,由牧人“扎西”从单纯的个人复仇猎杀生活,到被活佛慈悲感化,也是在神秘的洞穴,在石碟上获取能量后,转变为与狼共舞,并把恶狼转化为匡扶正义的力量,去剪除土匪、协助平息战争,实现了社会意义的英雄壮举,这些故事又是标准的英雄史诗——是侠肝义胆的人“扎西和王剑客”,借助某种自然力量,完成某种使命,小说最终赞美和弘扬藏族文化中勇敢、坚毅、慈悲、深情的优秀基因,谱写出草原各阶层共同造就的英雄故事。
神话时代与英雄时代兼备,由人群和某种灵性的动物群,在竞争与合作状态下完成的故事,小说在结构上,是以扎西为纽带的“神话时代”与“英雄时代”的双螺旋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在著名的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里,有精彩的表现。
三、人心与人性救赎的多层谱系
小说里整体赞美了一群以藏族为主的人物,涉及的人物阶层,比较全面,分别是朝圣者、牧羊人、杀狼牧狼人、管家、土司头人、盗马剑客、官差、传教士、修女、天葬师、麻风病人、办报文化人、京城大侠、军火商、黑帮等。在晚清社会巨变中,小说写出了一群人物命运的反转和人性的救赎,这种救赎,也是多个层面的展开来。
一是旺堆头人的女儿曲珍,从单纯的唐卡绘画修行的女子,在被土匪黄大郎挟持到土匪窝,屈辱地做了一年的土匪压寨夫人,被王剑客救回家苦练枪法,最后爱上并协助剑客王成汉一起行侠仗义,消灭土匪;又协助扎西率领的狼群,平息了草原部族战争。以侠义为导引,完成了一个从女孩到女侠的自我救赎。
二是喜喇活佛,在一定程度上是藏地文化代表,他不但用柳枝接骨法拯救了扎西的生命,还一再用“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的开示,在扎西从猎狼人转化为牧狼人的证悟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活佛本人,从不问世事,到勇敢对话土匪,联合政府主局调停多年的部落战争,保全了更多的生命,实现了佛家学说究竟根本的“弘法利生”的目标。
三是全篇最核心的自我救赎,由扎西的命运变化来表现,他误以为狼群祸害了自己的妻女,任凭自己的仇恨弥漫整个草原,大肆屠杀狼群。当逃出土匪窝的妻子告知自己和女儿并非狼群所害,痛苦的扎西愧疚到奄奄一息。从杀狼到养狼,人心与兽性共同的善,在这个点结合起来。一个执迷于私仇家恨的复仇者,反转为除暴安良的草原英雄。完成了英雄自己人性的救赎,也带动了狼性的救赎。
最具有家国情怀的人生救赎,当属多重身份的王成汉,此人一身武艺流落江湖,却是忠实的李白诗歌的拥趸者,这种双绝的气质,本身就是汉文化中“书剑飘零”者的典型形象,无论是他护卫马帮、还是沦落为盗马贼、都是大社会变迁下的小人物命运波折。他在接触《蜀学报》的宋育仁和见识过变法的罗金刚以后,书生与剑客遗传基因中的“经世济国”意识猛然觉醒,以至于他上北京唔见大刀王五、午夜祭祀六君子、千里拜谒谭嗣同墓。完成了一个求个人快意恩仇的侠客,向助力家国天下命运变革的义士转化,人生的境界豁然廓开,这是一层最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救赎。
四、诗性洋溢的稀贵写作
与一般小说家啰里啰嗦的语言风格不同,作为诗人的黎正光,无论是语言和结构上,都追求诗意的洗练。
比如,关于雪,草原的雪,第一章不同环节,他用这样的写法:
“寒风呼啸、雪花狂舞”/“雪花似银碟在夜空飞舞”/“风吹过茫茫雪原,远处雪山宛若银色金字塔默立蓝色天空下”,这种多次对雪的描写,除了铺排故事背景,更是把纯美的大自然与血仇污秽的人心对立起来,立即让故事画面具备了戏剧的矛盾冲突。
小说的诗意性还体现在对于人物意义的多重设置,譬如前文(三)提到,就是人性的救赎这一主题,小说就次第展现了曲珍、活佛、扎西、剑客四种层次的救赎。一部小说本身需要复杂的人物结构来表现主题,但《牧狼人》在“救赎与拯救”一个主题上的多层次展开,是我们在阅读小说纷繁复杂的情节之外,多了一层反复咏叹的诗意体验,这是这部小说跟其他小说的又一个差异化标签。
诗意的第三表现是神奇的比喻设置。那一只在关键环节反复出现在扎西和狼群眼中的“三尾红狐”,就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对人们的护佑或加持,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无法求证他是什么,但它就客观地出现在扎西最需要他的关键时刻,这个红狐所比喻的力量功德,特别象藏文化传统所一直崇拜、修习、证悟的力量。
这种力量支撑了主人公妻子卓玛的忍辱偷生,也促成了卓玛纵身向冰湖一跳。卓玛的自杀即完成了自己对自己屈辱的了结,同时也是活佛救治扎西,以慈悲力量开示扎西的缘起,这个细节的设置,具足了某种禅机。
正是这些语言、情节、意义和事件,构成了一部史诗的内核,象征、比喻、暗示、渲染的写作方式,让这一部小说,具有了别样的诗性特征,是稀有题材的稀有表达方式。
藏文化中的卓玛,是度母的名字,她不但具有女性的一切美丽和温柔,还有带给人长寿、富贵、权利、幸福的功德能力,更是像汉族人民信奉的观世音菩萨,周行于十方世界,救苦救难。小说用扎西妻子“卓玛”的遭遇,激发了一系列杀戮和救赎的故事,涉及到人群与狼群、僧界与俗界、战争与和平、个人与家国。在我们难以把握的人生命运里,难以描述的“业力”左右我们的命运,我们在小说里看到,贡布头人几次生起杀机,但他观望一下巴登送的“绿度母”佛像,心里的恶念就一次次熄灭。
今天,由现代著名活佛多识仁波切指导仪轨的精美绿度母,将在年后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消除那些无名的业力,带给更多人们救赎的力量。
欣赏小说《牧狼人》,观想绿度母佛像,也许小说给每一个读者,带来另一种诗意的救赎。

关于绿度母佛像有关详情,请阅读《遇见、多识仁波切心中的绿度母——新绿度母佛像校勘、开示记》,或扫描以下二维码咨询咨询

夏吉林,独立诗歌批评人,毕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多篇语文教学、诗歌、诗评发表于全国报刊。1997年起与人合作出版《第四代人的精神》《人民记忆50年》等社会批评著作。现居成都,负责“云端藏地”互联网新零售平台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