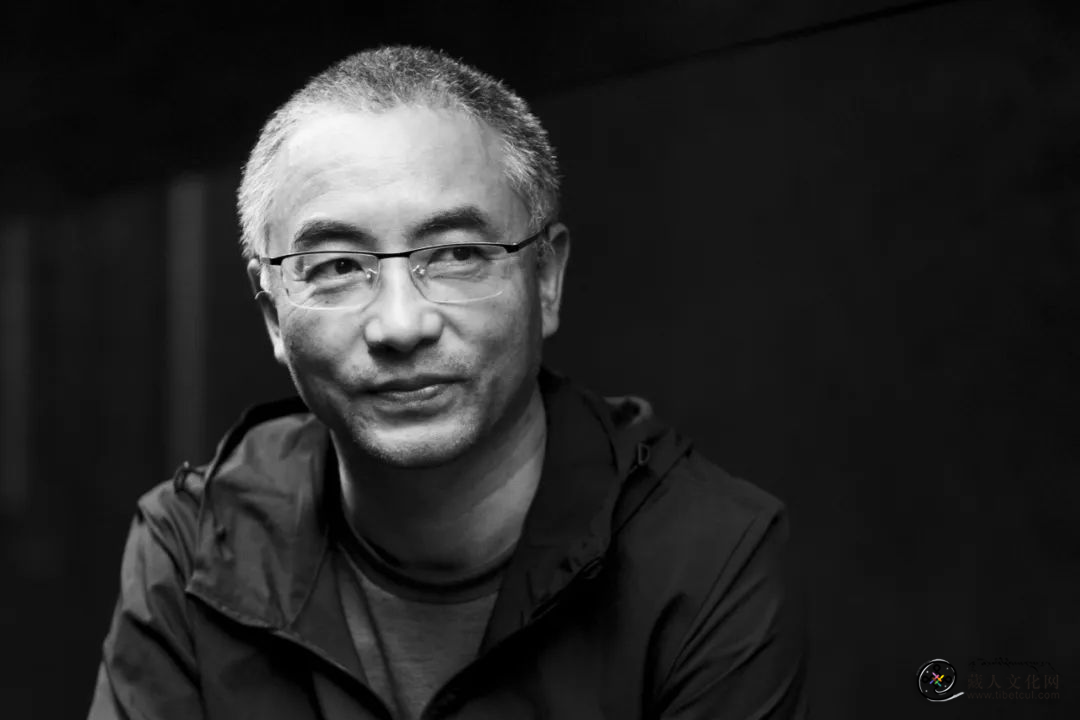在刚杰·索木东简洁朴实的诗句中,我们欣赏到了甘南独具特色的地理风貌,感受到了善良热情的藏族人民的美好品性,领略到了藏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的魅力,他的诗歌有一种回味无穷的“酥油茶”的清香味。

刚杰·索木东,又名来鑫华,藏族。1974年出生,甘肃卓尼人。有诗歌、散文等被译成英、藏、蒙古、维吾尔、朝鲜等多种文字。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范大学。
守望名叫甘南的那片草原
李玛
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的诗歌作品丰富,创作风格较为一致,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较有代表性。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强烈的故乡情结,表现出诗人对故乡的守望。在守望中,诗人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故乡,并在对故乡的书写中反观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以此丰富了诗歌的内涵。甘南这块“高地”成为诗人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使其诗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气息和哲理思辨色彩。
难以忘怀的乡情
刚杰·索木东曾说:“我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来自骨头里奔腾着的血脉。”这“血脉”就是作者的故乡情,是一个赤子对故乡自然风光、文化习俗、亲朋好友的无限思念、赞美、眷恋,这乡情犹如一条清澈而永不断流的小溪,滋养出了诗人的那颗洁白无瑕的诗心。
甘南位于我国甘肃省西南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境内有广阔的草原、惊艳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景观。诗人20岁时离开了故乡甘南来到兰州求学,从此与故乡“相聚”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但这并没有使他与故乡甘南的关系变得疏远淡化,反而使他的乡情更加浓厚。在《故乡是甘南(组诗)》《清晨,突然想到甘南》等诗歌中,诗人从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描绘了故乡的山水、人情和文化,在或柔美、或伤感、或激越的诗歌旋律中,尽情地倾诉了他难以割舍的乡情,使其诗歌具有了一种乡情美的审美特质。
乡情是诗人永远的心结。在对故乡的书写中,诗人终于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甘南那片纯洁、开阔、丰满的草原,与甘南融为一体。这种美的特质,对于刚杰·索木东来说,不仅代表着他的创作风格,更加表现了他温柔而包容的美好品格。他的诗歌表现的不是小我情怀,而是一种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把自己融入到了一切生命之中大我的博爱情怀,这样使他和他的诗歌抵达了另外一个生命的“故乡”,也因此有了广度和高度。刚杰·索木东的诗歌以难以割舍的乡情,感动了我们浮躁、迷茫、冷酷的灵魂。
难以排遣的乡忧
在刚杰·索木东诗歌里,甘南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诗人在一次次“归乡——离乡”的时间和空间组合中审视现实的故乡。在此基础之上,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的故乡,这又使他的诗歌在抒情中闪耀着一种理性的光芒,表现出一种更为高远、豁达的人文关怀情结。刚杰·索木东的诗歌既有对故乡挚爱、思念、赞美的浓烈情感,同时又有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故乡“变”与“不变”的思考和难以排遣的乡忧情怀。
面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城市文明不可阻挡的洪流,甘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生活在这片蓝天白云下的农牧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当诗人回到故乡面对眼前的“变化”时,故乡的一些人、事、物已和儿时眼中的不一样了,这使他感到陌生和担忧。在《甘南: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冬》中他这样写到:“一盆牛粪火燃起的冬天/阿妈刚把最后一粒种子/连同秋天一起收起/一场大雪/已经迫不及待地落满草原/冬天的甘南/羊皮袄捂不热的甘南/一个新的生命需要诞生/一个黑脸蛋的新娘坐守雪域/她和她黑帐篷般的幸福/像长夜一样漏风/在甘南/一首牧歌正逐渐生疏/一条老路正逐渐生疏/在第一个季节里/怀念的寨子/正逐渐生疏”。诗人由故乡的“变”而引起了思考,他一方面赞成故乡的“变”,推崇与时俱进、求变求新,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鲜的血液。但另一方面,诗人在诗中也表现出了担忧,比如城市消费观念的涌入,故乡曾经熟悉的迷人风光、淳朴的人性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着变化或消失。如《塔尔寺》中,“神圣的经卷中/衮本贤巴林/绛红色的僧衣/正在隐去/喧闹的塔尔寺/我只能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打铁,或者一个久远的印象》中,“三十年后,再次路过/街坊,那间打铁的屋子/富丽堂皇,迎面而立/一个妖冶的姑娘”;在《茶、马、或者远逝的古道》中写到,“而谁又在/将醒未醒的梦里/为我注入/母语丢失的历史”等等。“喧闹的塔尔寺”隐喻故乡在商业化的进程中已经变得世俗而浮躁;“一个妖冶的姑娘”隐喻故乡淳朴无私的人性的消失;“母语丢失的历史”隐喻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的改变或消失。这一切的变化或消失令作者在《甘南: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冬》中感叹:牧歌正生疏,老路正生疏,寨子正生疏,文字简练,节奏急促,真切地抒发了诗人对故乡这些本不该“变”的美好人、事、物发生改变时所产生的深沉忧患感。
游走于故乡与城市两地的诗人,不仅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般的故乡,同时也描绘出了一个贫瘠荒凉的故乡,这两种故乡在诗人的笔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乡。如《在甘南》:“高原最高的地方,那些/顽强盛开的鲜花都叫做格桑/那些黑脸膛的汉子/深藏着骨缝里的忧伤/一泓泉水流下山崖/那么多的传说,开始/风一般流行/是谁,又把贫瘠的甘南/搁在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云端”。故乡如格桑花一样美丽,如康巴汉子一样坚强,如传说一样神奇,但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在这些华美的外衣下“深藏着骨缝里的忧伤”,这“忧伤”源于故乡的荒凉贫穷,作者将目光转向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来“剖析”故乡,看到了故乡“不变”的一面。
由于甘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原因,造成了这里交通不便,导致当地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较差,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同时,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也进一步加剧了贫穷的延续。诗人在一遍遍的回望中叩问自己:“走出故里我就能摆脱困苦吗/甘南,遥望经年的故乡/贫穷苦难夜夜撕裂我流血的心愿/情所独钟的卓玛姑娘哟/紧握皮鞭的玉腕骨瘦如柴……”(《走出甘南》)诗人在诗中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希望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情况的脱贫致富之路,让故乡的人们早日过上幸福、文明、和谐的新生活。
难以忘却的乡思
刚杰·索木东自离开甘南藏区后,就长期在兰州求学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城市,诗人眺望远方的故乡,并用朴实的文字组成一首首包含着至真至美的诗篇,来抒发乡思之情。这种乡思在四季的轮回中被拉长,成为一根“剪不断”的丝线,一头连接着故乡,一头连接着漂泊异地的诗人。
在诗人笔端,乡思不仅是对故乡具体的人、事、物的思念,它有一种更深层的抽象内涵,是一种在现代文化观念熏染下的藏族知识分子的,对族群文化的“乡思”,更倾向于内心世界的思想和精神的层面。如《高原上的狼毒花开了》:“终于可以对这个午后说出暖意/终于可以,对那株变了色的狼毒/努力说出,我的赞美——/荒芜的大地,已经无需证明/你的根系,究竟有多么庞大/站在母语丢失的路口/也无法洞悉,那些/和骨头一个颜色的纸张/经世不腐的秘密/如你所愿,/这个夏天/高原上的狼毒又开得茂盛无比/——满山都是,统一/晃动着的脑袋”。狼毒花在诗中不仅仅是故乡特有的一种植物,更重要的是象征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一种顽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诗人在异乡想起高原盛开的狼毒花,不由得想到了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种更深层的乡思之情不禁从内心升起。
受到藏文化熏陶的诗人,成人后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来到了大城市,身处另一种文化群体之中,这样使他和故乡有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通过现代都市文化与“故乡文化”的比较,使他更加清醒地看清了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他曾在访谈中提及自己“不遗余力地努力诠释和传播着优秀的母族文化和个人情感”。这是诗人创作诗歌的一个原因,他要通过诗歌创作,从审美的角度完成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今生今世在诗歌中一遍又一遍念及那遥远而咫尺的故乡——甘南,在思念中回归故乡,再现优秀传统文化。
在刚杰·索木东简洁朴实的诗句中,我们欣赏到了甘南独具特色的地理风貌,感受到了善良热情的藏族人民的美好品性,领略到了藏族悠久灿烂的文化的魅力,他的诗歌有一种回味无穷的“酥油茶”的清香味,这种味道使他的故乡情结有了民族特色。从他的诗歌中,我们也看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重述本族群历史文化传统的精神需要。

李玛,现住拉萨。2006开始写诗,曾在不同刊物和网络平台发表过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著有诗集《诗意雪域,心灵家园》。
【创作谈】刚杰·索木东:人世温润,诗意而行
我出生在甘肃甘南。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这片土地,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青藏高原的窗口”和“藏族现代化的跳板”。从西羌到吐谷浑到吐蕃再到近代,历史上一直是多元文化交相映辉的地界,更是一片风格迥异、风骨独具的文学沃土。
在这片藏汉二元文化浸润的土地上,民间生活中充斥着古老的谚语歌赋,许多人开口即诵。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一个大字不识的老祖母,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充满着大智慧的谚语:“别急着念玛尼,先去做点念玛尼的事情”,等等。在百年老木屋那一排排因多年日晒而四处龟裂的檐柱里,我和兄弟姐妹们拿棍子掏出筑巢的鸟儿和结网的蜘蛛,顽皮玩耍的同时,也掏出了这个屋檐下牛一样苦累了几辈的女人们,梳头时塞进去的凌乱白发!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兄弟姐妹们开始知道了手握岁月的痕迹,感觉生活的艰辛和母爱的伟大。之后经年,母亲凌乱的白发就在我生涩的笔端,如一场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不分季节、纷纷扬扬地落下……
这些植根于血脉的东西,慢慢溶解在人近中年的生活和写作中,反复回味,受用无穷。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都从诗歌起步。我的文学之路亦是如此。之所以走向文学之路,往大里说,应该是神性和诗性始终弥漫着的青藏高原,给予了我和雪域大地上所有的族人,与生俱来的那种灵性和诗性。正是植根这片土地的优秀文化,让她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长久地持有一份豁达而宁静的内心——这恰恰就是文学乃至所有艺术最需要的。
母族文化是文学的源动力,民族性的表达是文学创作的缘起。只有在自己熟知的文化中汲取营养,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才能不断成长,才能实现自己的跨越,才能让自己的创作基于民族文化而跻身世界文化之林,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我的创作,也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和认知开始,并一直向这样一个高度努力和靠近。
在兰州读书、工作的20多年里,多元文化的滋养,让我自己慢慢完成了从“青藏咏叹调”式的单纯抒情,到“人世温润”的自然表达的过渡。自己的文字也慢慢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也就是说,当我们贴近母性大地,用“众生”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和学会表达时,创作就会超越自我,抵达一个前所未有的温润境地。
文学创作是超族裔、超人类的创作。我们之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族裔性的群体创作,恰恰就是在强调族裔性的同时,超越族裔性,也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概念。
毋庸置疑,在汉语语境中,作为藏族作家的“边缘感”和藏族文学中用汉语创作的“边缘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桎梏着自己的创作。但是,前进一步就会发现,边缘感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局限性认识,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不成熟的创作状态。因为在文学创作中,永远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别。如果一个作家的视野开阔了,创作成熟了,任何“边缘”都会成为“中心”。在真实的纪录和表达里,我们逐渐和母族融为一体,逐渐和人类融为一体,逐渐和世界融为一体。
原刊于《文艺报》2018年10月22日2版